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近日,为推进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发展高地,上海印发了《上海市促进高端医疗器械产业全链条发展行动方案》,其中提到创新医疗器械发展的目标——到2027年,新增首次获批境内第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超500件,新增在海外市场获批医疗器械产品超100件,培育年产值超100亿元,具备较强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2家,建设高端医疗器械产业聚集区3个。
创新医疗器械的发展离不开生态的发展。从欧美等发达地区的创新医疗器械发展的经验来看,医疗器械合同研发生产组织(CDMO)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自2021年《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来,医疗器械注册人(MAH)委托生产模式在全国开始推广。
然而直到今天,医械领域都还没有出现一家像生物医药领域的药明康德这样规模的合同研发提供商,且医疗器械CDMO仍局限于体外诊断(IVD)等低值医用耗材领域,为高值医疗器械提供服务的CDMO大平台在国内比较少见。

外包并非唯一选择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中国医疗器械供应链发展报告(2025)》,2024年我国医疗器械工业市场规模达1.2万亿元。不过,相较于生物医药行业而言,医疗器械行业的CDMO发展还面临多重挑战。
有业内人士将生物医药CDMO视为“重工业”,它服务于一个产品相对标准、单个产品市场价值巨大、生产规模效应显著的行业,因此容易催生巨头,形成大规模产业;相比之下,医疗器械CDMO更像是“精密手工业”,它服务于一个产品极度非标、市场高度碎片化、生产规模效应有限的行业,因此更倾向于专业化、分散化的格局,整体规模较小。
日前,在上海举行的2025国际医疗器械设计与制造技术展览会(Medtec)上,聚集了来自医疗器械领域的供应商。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其中也不乏一些国内提供医疗器械从研发到生产一站式服务的CDMO平台,包括水木东方、湃生科技等。
据介绍,湃生科技为医疗器械厂商提供高值医疗植入、介入器械业务,CDMO服务,产品管线涵盖神经介入器械、心脏介入器械和外周介入器械;水木东方是医疗机器人技术与产业协同的创新平台,为手术机器人等高端医疗器械提供CDMO服务。
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厂商中科鸿泰是在水木东方平台上成长起来的医疗器械公司,同时也是水木东方CDMO平台的使用方。例如该公司手术机器人的专用一次性耗材对生产环境(如洁净车间)要求较高,就委托给CDMO平台生产。
中科鸿泰总经理彭亮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CDMO平台提供了资金、场地、生产设施、产业生态等初创公司最急需的资源,极大地加速了产品从研发到临床的进程,能让企业少走弯路。”
目前,中科鸿泰的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产品已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绿色通道,计划在2025年第四季度启动多中心临床试验。
据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像中科鸿泰这样的手术机器人公司中,虽然有不少使用了CDMO平台,但还有一些厂商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厂房和团队,例如另一家已经拿证的血管介入手术机器人厂商唯迈医疗就没有使用CDMO平台。
业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外包服务已经成为生物医药启动临床和商业化的必然选择,这是因为大部分初创药研发公司通常没有财力自建符合GMP要求的生产设施。而对于医疗器械而言,外包服务的选择性极强,许多医疗器械公司,特别是已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倾向于自建产线以控制核心技术和供应链,外包动力更多出于成本效率、聚焦研发或获取专业能力的考量。
唯迈医疗创始人CEO杨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是否使用CDMO主要看企业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选择了。在产品注册阶段,如果不自建洁净车间以及相应的生产质控体系,委托CDMO平台生产,确实可以节省一部分成本,腾出精力和资金,但到了后期产品量产阶段,目前来看还是企业自己建设厂房和团队成本更低。”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医疗器械公司到了产品量产阶段会转移至自建生产体系,但杨贺表示,这不仅取决于企业与CDMO平台的协议约定,还取决于企业委托CDMO的具体内容,合作深度不同,后期转移生产自建的难度也不同。据他了解,最基本的CDMO委托的内容包括生产体系的建设、法规以及设施人员,而更深度的合作,则还覆盖特殊工艺、设计,以及一些涉及较强专业知识的内容(know how)。
商业模式尚未成熟
一位国内医疗器械上市公司董事长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来看,CDMO的商业化机会还面临一些瓶颈。前几年医疗器械行业百花齐放的时候,这些平台还有不少机会,但这几年发展有些放缓。”
他对比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CDMO的区分认为,在创新药领域,大部分的生产过程或流程是标准化的,有了新的药物分子后,设计、组分等剩余问题都可以外包给CDMO去做,但医疗器械涉及太多工程、材料以及专业知识,创新医疗企业有很多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机密,因此从商业模式来看,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难度较大。
医疗器械专家、上海理工大学健康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宋成利曾在英国邓迪大学(University of Dundee)医学院从事微创医疗器械及技术的研究,他回国后积极推动医疗器械领域的产学研合作及创新创业,主持教育部现代微创医疗器械及技术工程研究中心的工作,并孵化了多家医疗器械科技公司。
宋成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医疗器械产品的复杂性高,器械品类千差万别,涉及多学科的交叉,例如材料、机械、电子、软件,是一个工程化的问题,这与药品有本质的不同,因此搭建CDMO的全平台非常困难,需要巨大的投入。”
在他看来,医疗器械单品的市场规模与药品相比相差好几个数量级,这也是医疗器械外包服务规模难以起来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单个器械产品的生产批量通常远小于药品,导致单个产品的成本高,CDMO平台接单的产出相对投入而言可能不高。”宋成利分析称。
他进一步说道,在这一背景下,CDMO要追求盈利较为困难,如果没有资金的持续支持,很多平台就会活不下去。“一方面是解决资金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内CDMO的发展模式也应朝着专业化、特定领域去发展,并且进一步加强产学研校企生态合作。”宋成利表示。
国家医疗器械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副会长姜峰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医疗器械委托人制度是国家局多方调研吸收后推出的有重大意义的好政策,是发达国家医械初创公司的主流业务模式,但国内难以发展起来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平台没有遵守行业规范,打破了生态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
“CDMO可以看作是代工平台,就好比苹果委托富士康生产iPhone这种模式,但国内有一些CDMO平台,‘见钱就动’,看到给别人做的东西卖得好了,就不甘于只做代工了,最后自己也利用客户的专利技术去注册生产医疗器械,变成了客户的竞争对手,客户对CDMO 平台的信任度也成为委托许可人制度推广的一大障碍。”
也有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一些CDMO平台开始自己生产医疗器械也是迫不得已。一些平台面临客户流失,产线闲置,为了活下去,自己生产销售产品也是一种方式。
姜峰认为,CDMO要做大做强,正确的发展策略应该是严格遵守道德准则保护客户知识产权,并努力提升服务专业度,在一定的产品领域内往上下游延伸服务。
“上游可以去做一些采购供应链的管理服务,以及产品优化和工业设计;下游可以延伸到代工产品检测和注册服务,有些代工平台运营团队自身都没有过从研发到注册全流程经历,就靠政策补贴和收费来盈利,这也导致委托许可人制度具体运营更加复杂。”他说道,“唯有专业合规的服务才会让这一制度进入良性循环。”
他进一步称,当前器械CDMO代工平台实现普遍盈利还非常困难,还是要部分依托政府的支持,政府持有CDMO 平台资产,请专业团队非盈利化运营,这样能让客户更放心,通过平台服务建设产业生态实现产业聚集,政府可以通过平台收入和落户企业税收等方式逐渐回收投资,这可能是多方合力推进委托许可人制度的好方法。
市场分工仍是大势所趋
相比之下,欧美医疗器械经过数十年发展,已经形成了高度专业化和细分的成熟生态,CDMO已成为医疗器械创新链条中默认且不可或缺的一环。而这背后的推动因素是美敦力、强生、雅培等大型医疗器械公司的发展需求。这些大公司为了聚焦核心研发、降低成本和加速创新,会主动将非核心产品或特定环节外包,整个行业分工合作的势态显著。此外,这也得益于西方国家完善的IP保护机制和成熟的法律营商环境。
在Medtec展会现场,第一财经记者也发现了一些来自全球的CDMO平台,例如Zeus和安费诺医疗(Amphenol Alden),前者是心脑血管医疗器械导管组件的CDMO。
Zeus相关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Zeus在全球市场针对美敦力等大客户提供CDMO解决方案,而其在中国的业务更侧重于提供导管等核心材料的供应。
上述人士称,近年来,国内也迅速崛起了一批CDMO平台,并趋向成熟,一些中小型的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也会转向国内的CDMO平台。“目前中小客户转向CDMO的相对较多,因为他们产品生产数量少,成本比CDMO高不少,这样CDMO就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表示,“降成本是国内客户目前最主要的诉求,过去他们会尽量向我们采购全部的原材料,但现在更趋向于仅采购我们的核心产品。”
他认为,医疗器械的制造与手机、新能源汽车的模式有相似之处,原型打烊后快速迭代开发,而未来的发展必然趋势是从纯代工到设计创新发展。
多名业内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大部分刚刚起步的初创医疗器械公司而言,CDMO确实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的痛点,但同时他们也会有知识产权方面的担忧。
启维医疗总经理周剑钗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该公司原计划想委托国内某CDMO平台进行研发、工艺验证、生产和注册,但经过企业进一步的规划,认为还是应该建立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决定自己搭建团队做研发及工艺验证等关键工序。
他进一步称,在与CDMO合作过程中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一般双方都会有约定,比如由品牌方提前写专利,而在研发和生产过程中相关的知识产权归CDMO平台居多,具体情况双方商量协定。
周剑钗认为,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是大势所趋,行业逐步有序发展的CDMO,是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方面。
杨贺也表示,总体而言,随着产业分工的细化,国内器械CDMO的专业能力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验证,企业选择尝试与CDMO合作的方式建立新的产品管线也将成为未来创新医疗器械的发展趋势。
曾在强生、波士顿科学等跨国企业担任高管的健适医疗创始人CEO王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未来随着中国生产能力的集中、比较优势在医疗器械领域得到进一步认可,以及中国医疗器械企业的规模和质量管理体系的提高,CDMO的发展也会迎来更大的机会。”
宋成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从长远来看,任何一个行业都是需要分工合作的,企业不可能凭借一己之力把所有的事都干了,那样成本会很重。“随着CDMO平台的发展迭代,未来将提供更多优质专业的服务,总会催生一定的市场需求。”他说道。
CDMO平台的发展也有助于帮助中国医疗器械加速走出国门,输出海外市场。第一财经记者也注意到,已有一些CDMO平台开始在欧洲等地建立研发制造中心。今年早些时候,专注于介入和手术机器人耗材的CDMO企业索特医疗(Salt Medical)位于爱尔兰的国际研发制造中心揭幕。爱尔兰也聚集了美敦力、波士顿科学、强生、雅培等众多跨国医疗器械公司以及全球知名的医疗器械CDMO企业。
索特医疗CEO张一博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希望借助这一平台,为中国本土优秀的医疗器械企业搭建通往国际市场的桥梁,帮助他们在全球化布局中赢得先机。”
张一博认同王欣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医疗器械CDMO一定要融入全球供应链中,发挥比较优势,才能发展壮大。索特医疗一方面通过中国优质成熟的供应链、代工资源,向全球的客户提供具有高性价比的一站式CDMO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也帮助中国器械企业通过生产制造出海,提高医疗器械产品的海外竞争力。
“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各国关税及当地的采购政策时,越来越多的中国器械公司会选择本土化的生产策略,但在海外招人建厂对于很多公司而言,投入巨大、时间成本高。”张一博说道,“这时,把产品交给专业的医疗器械CDMO就能提升效率、降低成本。”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外资CDMO纷纷易手,它们在华消失殆尽了 | 海斌访谈
“这个领域已经证明,中国效率比美国要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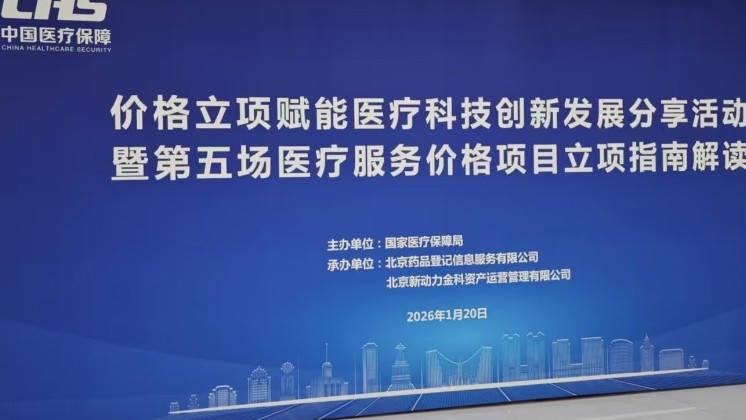
国家医保局首次明确机器人手术收费指引
机器人手术已经成为医疗精准化的代表。近年来,手术机器人企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产品上市获批速度越来越快,医疗机器人在参与手术的过程中如何收费是业内高度关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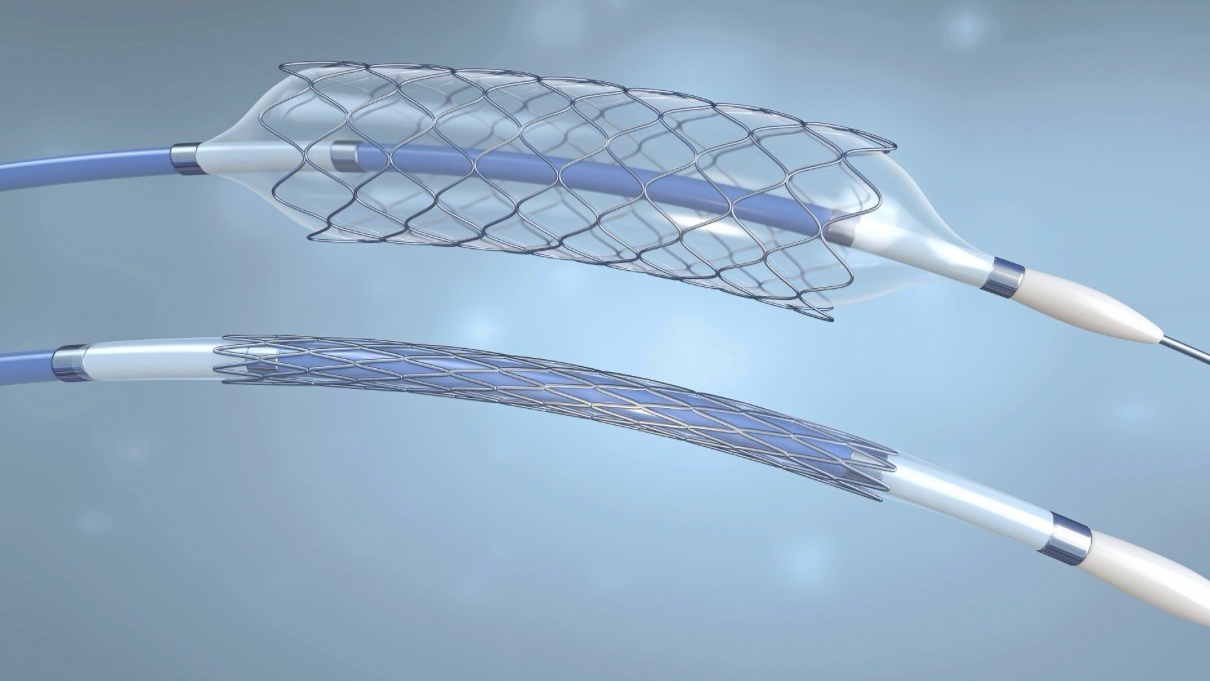
新一轮集采后冠脉“硬通货”大降价!近万元药物球囊普降至两千多元
自冠脉支架集采落地后,药物涂层球囊用量上涨显著,是公立医院心血管病科最重要的手术高值耗材之一。

这一医疗器械在美国高度垄断,“瓣膜之王”收购遇阻!中国市场百花齐放
心脏瓣膜因研发壁垒高,一直被视为医疗器械皇冠上的明珠。在全球市场上,头部企业主导市场的趋势日益显著。

李西廷2亿增持迈瑞医疗,名下持股平台曾套现超百亿
半个月已经买完,增持不到总股本千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