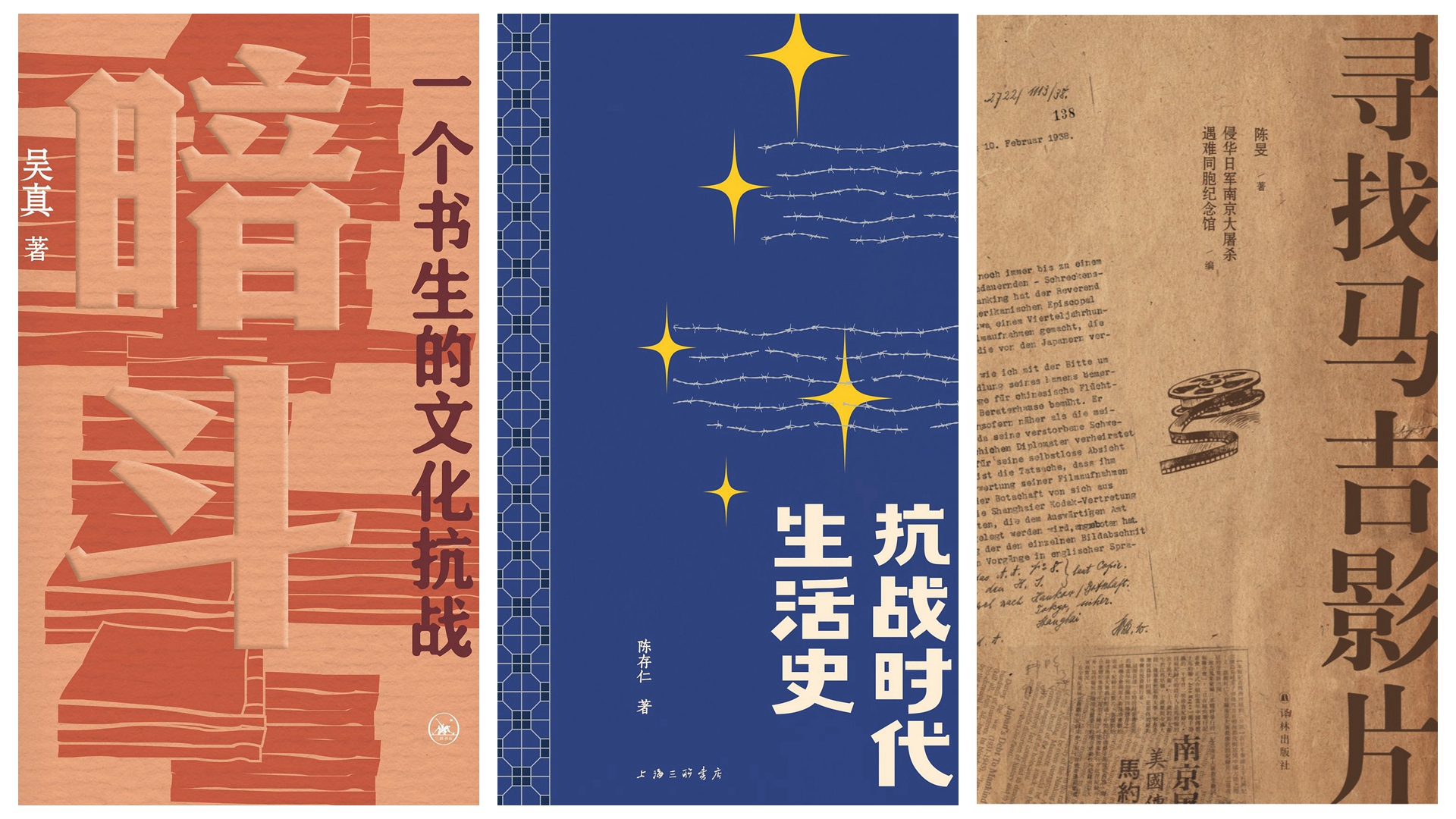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1938年底,中央大学一位管理牧场的工作人员,在南京沦陷前4天,以游牧加坐轮船的方式,历时近一年,把畜牧兽医系里珍贵的实验品种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等动物,从南京辗转转移到重庆时,全校轰动了,师生们站在临时校门前的道路边鼓掌欢呼,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
提到抗战时期的大学内迁,多数人想到的就是西南联大。实际上在当时,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同济大学、东北大学、中山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华中大学、中央大学等名牌大学,都在战火纷飞中南迁到广西宜山、贵州湄潭、四川乐山和宜宾、云南喜洲、陕西汉中等地方,形成了世界教育史上罕见的战争中的“流亡兴学”。
“很多大学后来不存在了,比如中央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华中大学,那段内迁的历史就快要被遗忘了。”2017年3月开始,作家聂作平自费踏上一段长达数年的寻访,最终写下了《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一书。

遗憾,很多历史已无痕迹
聂作平的写作始于一个电话。2016年,央视科教频道的一位编导想拍一部纪录片,邀请他写气象学家竺可桢的故事。看竺可桢几百万字的日记时,他在贵州办学的经历引起聂作平的兴趣,他打算以竺可桢日记为线索,重走浙大西迁路,写一篇关于浙大西迁历史的文章。
2017年3月,聂作平从成都驱车出发,去的第一个地方是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1940年初,随着北部湾失守,浙江大学启动第四次迁移,来到云贵高原深处的小城遵义、湄潭和湄潭下属的永兴镇,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迁回杭州。
在湄潭,聂作平看到浙大学生曾经上过课的湄潭文庙,寻找到已成危房的老建筑万寿宫,它曾是浙大研究生院所在地,也是曾经的中央实验茶场场部。他还去看了湄潭的茶园,浙大迁到湄潭后,农学院教授刘淦芝指导学生对湄潭茶叶做了全面调查。湄潭城里,也打下了浓厚的浙大印记:可桢路、浙大北路、浙大南路、浙大小学,等等。

浙大在湄潭,是抗战时期大学内迁的缩影。“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首先内迁,此后近十年,北方和东部沿海城市迁往西南的大学有十余所,师生们一路穿越战火,颠沛流离,甚至还有很多人员伤亡,可谓历尽艰辛。
“华中大学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它的内迁之地最后在洱海附近一个叫喜洲的小地方,是所有内迁大学中,迁得最遥远、最偏僻的一个。”聂作平说。1938年,华中大学从武汉迁到桂林,但桂林遭到日军轰炸,只得再迁往此前绝大多数师生都没听说过的喜洲。为了安全,师生们甚至从镇南关出境到越南,坐火车到河内,再从河内坐上去昆明的火车——当时滇缅公路尚未通车,河内到昆明的铁路是中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

1937年至1939年期间,同济大学五次迁校,在昆明的时候没有安置的地方,只能分散在昆明及周围12处,是所有内迁大学中拆分得最零散的。中央大学被誉为“民国第一高校”,在内迁大学中是比较顺利的,1936年日本策动华北五省自治的“冀东事变”之后,校长罗家伦就下令制作了900只大木箱,做好迁校准备。“七七事变”后,他意识到大规模的战事一触即发,于是在1937年8月顶住重重压力,直接把学校迁到了重庆沙坪坝松林坡。
不过,中央大学已经消失了几十年,它留在重庆的历史痕迹已不多。松林坡上如今种满南方常见的黄桷树,只有重庆大学校园里的大礼堂,才是当时的建筑。这些年虽到处寻访历史踪迹,聂作平总觉得遗憾,“做这件事太晚了,很多痕迹已经没有了”。
逃亡路上师生留下大量记载
聂作平的老家在川南一个乡镇,靠着一支笔写到成都,作为体制外的职业作家,他天然地对动荡时代中,人在历史和命运面前的选择感兴趣。
“以前我们对竺可桢的了解,来自中学语文课《大自然的语言》,觉得作为气象学家的他是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我看了他的日记,重访了他内迁时生活过的几个地方,也采访了他的儿子,感受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立体的人,有情感,有痛苦。”聂作平说,竺可桢在江西泰和上田村的经历让他印象非常深。1938年7月,在广西寻找新搬迁地址的竺可桢,接到电报后匆匆赶回泰和。到家才知道,儿子和夫人都染上了痢疾,因为缺药,先后病逝。竺可桢悲痛不已,妻子下葬时,他将1933年在美国买的一块手表和一支钢笔作为陪葬品放入棺中。安葬好妻儿后,竺可桢带着另外几个孩子,匆匆和浙大师生前往千里之外的广西宜山。
“九·一八”事变次日早上六点,东北大学秘书长兼代校长宁恩承召开全校大会,宣布解散所有师生。他发还学生的伙食费,宣布男生自行解散,女生在沈阳没有亲戚的,暂时安置在苏格兰人开办的医院。他在会上说:“我在英国上过学……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乘客,再次是船工水手,最后是船长……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筹划安全出险办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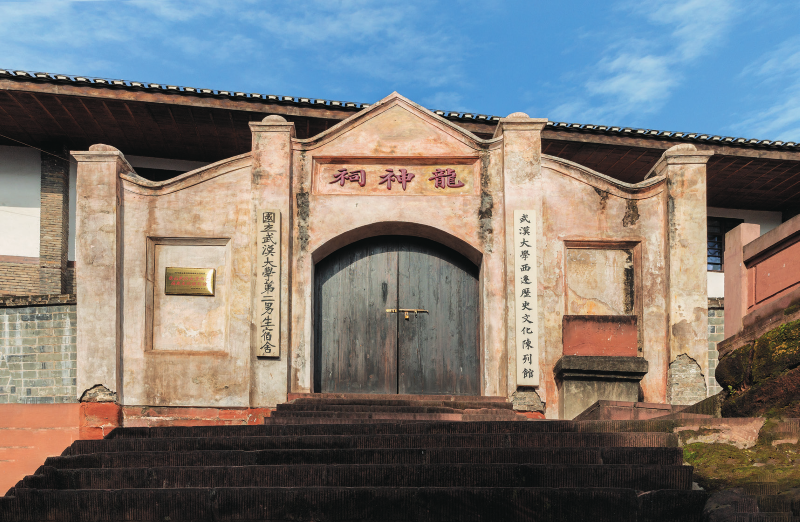
《山河万里》一书也通过亲历者的访谈和他们留下的大量历史记载,呈现山河破碎时,生灵涂炭的惨状。东北大学学生徐景明从沈阳逃往北平时,挤上一辆运煤车。火车开了一段,突然停下来,车厢里的一个妇女抱着一岁左右的孩子,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车窗边,把孩子伸到窗外大便。没想到火车突然启动,孩子掉下去了。“孩子的妈妈哭叫着要往外跳,被旁边人拽住。于是孩子母亲揪头发,捶胸大哭……”火车开着开着,车厢里的人发现,有血从车顶流下来,原来车顶也挤满难民,过隧道时,他们的头撞到了洞顶……
他们照相时都表情从容淡定
尽管时局动荡,颠沛流离,内迁的名校并不封闭,想尽各种办法保持与外部世界互动。作家齐邦媛在《巨流河》中记载,美学家朱光潜在乐山为武汉大学学生上英诗课时,用的教材是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1944年,著名学者李约瑟在福建长汀看到,内迁至此的厦门大学图书馆的书不仅没有损失,还添购了大量新书和杂志,藏书量达到8万册。
那几年,很多学者也做出了一生中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在贵州湄潭,数学家苏步青白天上课、种菜,晚上点着油灯写论文,4年左右时间发表了31篇论文。“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淦昌到湄潭郊外的实验室工作时,要牵上一只羊,这种情况下,他写出了论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一个建议》,在美国《物理评论》发表后,立即引起美国同行的重视,这也是他早年间最重要的一项研究工作。

也是在湄潭,17岁的李政道经常去听王淦昌,以及中国理论物理学家、中国雷达之父束星北的课,并在束星北的建议下,从浙大化工系转到物理系。1944年,李政道想弃笔从戎,遭到束星北的极力反对。他认为李政道有物理天赋,以后必定成栋梁之材,谁都可以当兵,唯独李政道不能。当时束星北在重庆出差,生怕李政道一走了之,着急地给王淦昌发电报,要求他一定要把李政道拦下来。
“那些知识分子都信奉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哪怕在战争中,他们的研究都不是只停留在象牙塔,而是和暂栖地的社会历史紧密关联。”聂作平说,华中大学利用地处云南边疆的优势,创办了西南边疆文化研究室,每年都有报告寄给美国哈佛-燕京社。学者包鹭宾第一个提出“白族”概念,证实了白族和傣族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当时国外很多学者把两者混为一谈,还认为南诏及大理国是泰国建立的。
“虽然当时日本一度在军事上占优势,但是中国的精英阶层都相信,只要用时间换空间,中国一定能赢。”在翻看内迁师生留下的照片时,聂作平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虽然颠沛流离、生活困顿,但都表情从容,面带微笑,“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坚守”,聂作平说,这也是抗日战争最后以中国胜利告终的原因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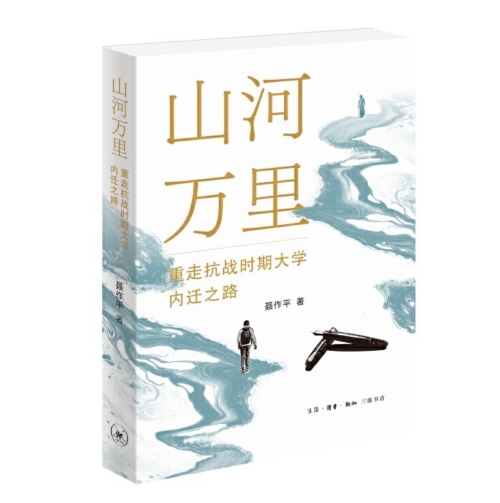
《山河万里:重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之路》
聂作平 著
三联书店2025年9月版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