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
每一个中国男孩,几乎都是从《三国演义》开始了解本国历史的。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从邻居家的旧书架上捞到一本泛黄毛边、繁体字版的《三国演义》,展卷阅读,罗贯中先生的第一行字就把11岁的我给镇住了:“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一直到30多年后,我才突然想起要问罗先生一个问题:“为什么天下大势,必须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可以分了就不再合,而合了就必定会再分呢?比如美国,1776年建国后就没有再分过,而欧洲在罗马帝国分裂后就没有再合起来过。“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美国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专家魏斐德甚至将它看成是西方历史与东方历史的“区别点”。
中国与欧洲在早期都是从部落制进化到了城邦制。到公元前360年,东方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集权式变法—商鞅变法,西方则在公元前356年出现了亚历山大帝国。到公元前156年至公元前81年,汉武帝完成了中央集权制度的试验,西方的凯撒大帝也让高度集权的帝制替代了共和制。
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3世纪,东西方世界分别出现了双峰并耸的、大一统的大汉王朝与罗马帝国。到公元184年,汉帝国陷入内乱,罗马帝国也在外族的侵略下分崩瓦解。
之后,东西方历史突然开始了“大分流”,中国在公元589年重新实现了统一,并从此再也没有长期分裂过。而欧洲进入中世纪,经历了漫长的封建制,便再也没有统一过。尽管在2000年出现了欧元,实现了货币意义上的“统一”,可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关于欧元的存废又成了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魏斐德的问题正是:“在世界第一批帝国—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为何差异起来呢?”
这似乎是一个很难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悬案,魏斐德给出的答案很简洁,但在我看来却非常精准,他说,“统一是中国的一种文化”。
中国人最害怕、最不能容忍的事情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是考察所有治理技术的边界。若将这个汉字组合拆解开来,统者“归总”,一者“划一”,在这个词组的背后隐隐约约地站立着一些让人望而生畏的“怪物”:集权、独裁、专制。这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别无选择。
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使得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对集权的容忍度远远大于其他国家。而这种国家治理逻辑显然与西方在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原理,存在内在的冲突性。
自由化的市场经济变革势必将削弱中央的集权能力,最近两次短暂的放权型变革试验—即民国初期(1916年至1927年)和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至1993年),尽管刺激了民间经济的高速发展,然而都没有寻找到维持社会稳定的药方。尤为可怕的景象则是,若分权失控,一些边疆地区出现独立事件,则更是任何改革者所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我们必须理智地承认,“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
这是一个十分痛苦的结论,也许我们这一代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找到其他的抉择。所以,一个保守性的结论是:在看得见的未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很可能是一次以自由市场化为取向、以维持“统一文化”为边界、在宪政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妥协点、非西方式的改革。内在的冲突性与生俱来,并且难以根本性解决。这次变革的时间长度很可能超过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长度!
如果不想错过一财网的独家报道和独到分析,您可以在微信上加一财网为好友:

历史学家许倬云去世,他研究的落脚点总是普通老百姓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于8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从卢布走过的一个半世纪,透视俄罗斯政治变迁
当今,俄罗斯并不是主导性的金融强国,但在大宗商品交换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使卢布仍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开埠前的上海并非小渔村,唐宋已是贸易港口
“上海史前文化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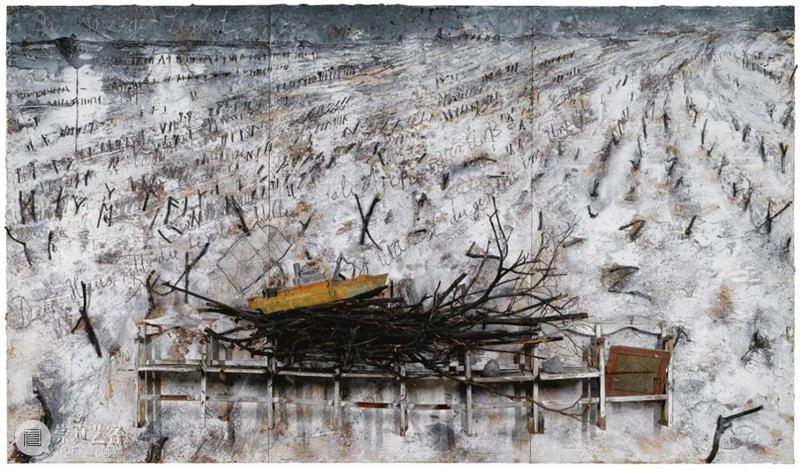
战后德国如何重塑自信、与过去达成和解?
钦文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领国,对德国的教育政策,包括中小学的教育大纲等影响很大,对德国历史的解释基本贯彻了反战的、和平主义的、反思纳粹专制的教育方针。

6000年前最初的上海是什么样
上海史前文化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这一发展历程与长江三角洲其他区域基本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