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1971年6月21日,一本叫做《全球概览》的杂志召开了停刊派对。杂志创办人斯图亚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邀请了小丑表演和混搭音乐演奏。他自己身着黑色修士长袍,赤脚在人群中走来走去。活动中,布兰德拿出两万美元现金。这是《全球概览》出版的收益,布兰德邀请大家上台讲述自己的设想,并可以取用一部分现金去实现它。布兰德宣称,虽然这本一共出版六期的杂志已经停刊,但是这笔钱将会是种子,而种子在这一天已经播下。
2005年,时任苹果公司CEO的史蒂夫·乔布斯来到斯坦福大学向毕业生演讲。在这次演讲中,他提到,有一本他们一代人的圣经《全球概览》,并引用了最后一期封底的题词:“保持饥饿,保持愚蠢”(Stay Hungry, Stay Foolish)。这场演讲非常著名,这句话也一度被认为是乔布斯本人说的。还好,这一次引用提升了很多人刨根问底的兴趣,去追寻那粒种子。
《数字乌托邦》就是这样一本追根溯源的书。自从乔布斯引用之后,国内出现了不少提及《全球概览》的文章,但是往往材料单薄,其中一些甚至出现了不少错讹。本书的作者弗雷德·特纳 (Fred Turner)是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教授,在资料运用上,从20世纪60年代反文化运动,到如今的计算机文化,可谓丰富。仅仅认为60年代孕育的种子,在21世纪成长为科技创新的参天大树,这种看法未免太过简化了。通过阅读这本书,我们反而能从大量的细节中,看到一系列事件,以及文化变迁的不同侧面。
尽管《数字乌托邦》不是布兰德的私人传记,但记录的事件还是围绕他和他身边的一群人。斯图亚特·布兰德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据他回忆,从童年开始他经历了对核战争的恐惧,而青春期又对冷战时代美国强大的军工联合体心存厌恶。先是美苏对峙,后来又是越战,战争与死亡一度是那个时代的底色之一。不管是随波逐流,还是如鱼得水,他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在60年代迅速投入了风起云涌的反文化运动。
建立公社,出版刊物,组织演讲,以及尝试迷幻剂,一代迷茫的年轻人通过这些方式寻找出路。布兰德很快成为了运动的积极分子。那时,建造穹顶建筑的巴克明斯特·富勒和研究传播的马歇尔·马克卢汉还是青年思想领袖,享受着先知般的推崇,而数字技术正在萌芽之中。
和《全球概览》关系最为紧密的活动恐怕要数公社运动了。不少年轻人在乡村地区成立公社,集体居住,实践他们的政治理念或者宗教信仰。1966年,布兰德意识到可以出版一本书,既是杂志也像邮购目录,为这些散居在美国各地的公社提供工具目录和精神养料。于是,凭借着剪刀、胶水,他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编辑第一本《全球概览》。这是一本制作精美的邮购目录,每一本图书、每一个商品都附上图片、编辑撰写的推荐语和购买方式。乔布斯称之为那个时代的Google,也确实如此。“全球”二字是名副其实的,它致力于提供一种“全球视角”,第一部分的名字就是“理解完整的系统”。它试图教会一个人,不要成为螺丝钉,而是真正学会建造太阳能热水器、记账、搭建帐篷,以及阅读生态学著作或者道德经。“全球”还和一个小小的运动有关。布兰德和朋友们发起了请愿活动,要求政府公开太空探索中拍摄的地球全图。当普通人第一次看到这颗星球的全景时,美国和苏联,白人和有色人种,这一切差异显得有点可笑。
尽管如今看来,当年的理想主义活动不乏讽刺的意味,例如《数字乌托邦》的作者指出,“遥远”的越战、近在咫尺的有色人种问题,以及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似乎这些事情都没有进入《全球概览》编辑们的视野。之后,一系列运动也随着70年代的来临而枯萎。越战结束,经济变迁,最重要的是人们已经不再年轻。从第一期收录的98种商品,到最后一期1072种商品,经历六期之后,《全球概览》宣布停刊了。
然而布兰德们还是那些长不大的孩子,他们开始关注黑客运动,发起家酿计算机俱乐部。1982年,布兰德推出了不成功的软件目录杂志,1985年,又和合伙人制作了“全球网络链接”(WELL)。布兰德本人始终不是成功的管理者,他的兴趣多变,除了黑客文化,他还关注太空探索、生态保护。新世纪,他创立了万年钟项目,写作了新的书籍,如今还活跃于复活灭绝动物的项目中。但是属于他个人的鼎盛岁月已经早早过去了,这里只剩下一个“如果种子不死”的问题。
好在,种子发芽了。WELL项目影响了最为早期的网络文化,在国际互联网出现之前。后来创办《连线》杂志的一批人在“全球”系列的影响下成长起来,90年代终于变成了互联网创业的弄潮儿。当年被《全球概览》启发的年轻人不仅有乔布斯,还有发明了图形化界面等一系列技术的施乐帕罗奥托研究中心的工程师。发掘意见领袖,把聪明有趣的人混搭在一起,出版(现在是网络版了)文章,后来的《连线》乃至如今还风头正健的TED大会,都能发现一点当年反文化运动的影子。也许最重要的,还是反文化运动影响了一批计算机技术的先驱者,而后来这批人成为了伟大的发明家和企业家。
那么,可以说如今的数字技术产业是这场运动的亲生子么?尽管有的人希望这样认为,仿佛想要发现父亲的文身——他当年也是超酷的。但纵览全书,答案却是复杂的。计算机技术并不会从反文化运动中自发生长出来。从一开始,很多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就是在反文化运动厌恶人的军工联合体实验室里,在拿着巨额国防投资的大学中。而之后,这些受到影响的年轻人,日后的路径,也离不开投资公司、媒体曝光,以及名利场效应。更为讽刺的是,个人计算机在70年代曾经是反体制和个人权利的象征,互联网也寄托了很多人关于平等和自由的理想。然而如今,当年的年轻人已经成长为行业大佬;而最大的“全球概览”——互联网本身,也处于“棱镜门”的阴影之下。
尽管如此,追溯还是必要的。这粒反文化的种子并不一定能一木成林,然而确构成了当今文化生态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全球视角”的思维方式、对信息流动的信仰,已经植入数字文化弄潮儿的基因。对于中国人来说,从邓小平时代“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号召开始,我们进入数字时代的路径与心态是如此不同。而如今,各种模仿掺杂着本土化的出版物、沙龙也已经太多。《数字乌托邦》的意义不仅是学习历史,也让我们看到那些学来的方法作为传统,是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因此,这本书不光是一本过去是怎么回事的书,它确实能回答一些关于未来的问题。

历史学家许倬云去世,他研究的落脚点总是普通老百姓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于8月4日在美国匹兹堡去世,享年95岁。

文弱书生,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男性气概是怎么形成的
“文弱书生”的出现,是男性气概的“去势化”的一个集中体现。

从卢布走过的一个半世纪,透视俄罗斯政治变迁
当今,俄罗斯并不是主导性的金融强国,但在大宗商品交换体系中的独特地位,使卢布仍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开埠前的上海并非小渔村,唐宋已是贸易港口
“上海史前文化从距今6000多年前开始,经历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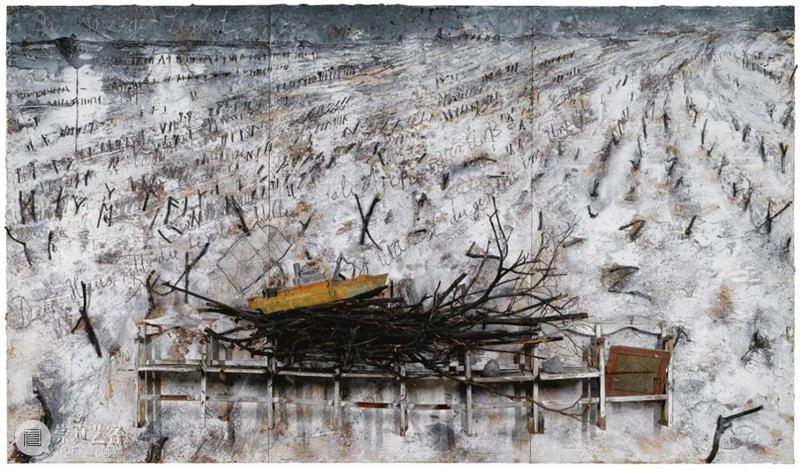
战后德国如何重塑自信、与过去达成和解?
钦文谈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占领国,对德国的教育政策,包括中小学的教育大纲等影响很大,对德国历史的解释基本贯彻了反战的、和平主义的、反思纳粹专制的教育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