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安德鲁·米勒半调侃式地回应外界对他作品的解读,“我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梦境。”
日前,应英国领事馆邀请,作为“英国新锐文学之旅”文化交流项目的作家之一,安德鲁来到中国,与包括阎连科、王安忆、孙甘露在内的中国作家进行对话。
18岁那年决定当一名作家
安德鲁·米勒出生于英格兰西南城市布里斯托,并在乡村中长大。回忆起小时候对文学的启蒙,安德鲁印象最深的是那种游离在现实和梦境中的精神状态。“看完故事书以后我总是在幻想,幻想一切和小说故事有关的事情,有时候是绚丽的场景,有时候是人物的模样——这种梦境般的幻想不间断地出现,让小时候的我分不清到底哪边才是真实的。”
这种梦境式的思维方式一直伴随着安德鲁成长,文字对他而言成为了一种特别的存在。“我清晰地记得是在18岁的暑假的某个下午,突然我就决定要做一名作家。”不久,安德鲁便离开了家乡来到了城市。
只是安德鲁并没有像小说中的青年才俊一样初出茅庐便光芒四射,相反,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餐馆炸鸡。在之后的10多年里,他还做过机场处理油污的清洁工,到工厂做杂役,甚至做过精神障碍者的看护。“事实上我很喜欢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只需要机械地付出体力劳动,而我的精神是自由的,我仍然可以用那个‘梦境’来思考生活。”当听到孙甘露在出书之前也有过近十年的邮递员经历时,他笑着说:“你看,这是典型的作家成长轨迹。”
1997年,这个蛰伏了近二十年的人生轨迹终于在安德鲁出版第一本小说《无极之痛》(INGENIOUS PAIN)后直线上升。《无极之痛》在1997年获得了英国和意大利颁发的两大文学奖项,在1999年更是获得了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
“刚拿到样书的时候我就像回到了孩提时代的圣诞节,那种难以消受的兴奋甚至让我感到有些身体不适。”安德鲁坦言,每次回忆起带来巨大转折的那一年,那种令人汗涔涔的侥幸都会让他自己愈发觉得不真实。“要知道,小说写到末尾的那个冬天,我必须把破电脑放在暖片上加热一会儿才能正常工作。”
让梦境与现实为邻
小说《无极之痛》讲述的是一位自小没有痛觉的男孩詹姆斯奇诡而短暂的一生,他在毫无痛楚中来到世上,却又在第一次感受到心灵剧痛后孤独离开。对此,包括英国《星期日电讯报》在内的多家报纸都曾以“超凡脱俗”之类的词语评价安德鲁的想象力。安德鲁半调侃式地解释说,“那是因为我有一个随身携带的梦境”。
在他的小说里,“梦境”永远与安德鲁所经历的现实联系在一起。从天赋异禀的男孩到历史上有名的风流浪子,再到乡村中垂垂等死的病妇和踌躇于战场的日本青年,安德鲁每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截然不同的。纵然如此,你还是能够在某些细节中找到小说与现实的重叠:《无极之痛》的主人公最后成为了一名医生,那是因为安德鲁的父亲就是一位乡村医生;风流浪子原本在伦敦和巴黎招蜂引蝶,却被作者“特意拉到了英格兰的乡下”;至于日本,那也是安德鲁曾经旅居过的地方。
谈到日本,安德鲁就开始滔滔不绝。“从18岁那年读到三岛由纪夫的自传开始,我就对日本文化中刹那绚烂的樱花文化着迷不已。”在最新的一本小说《一个快活的清晨》中,主人公高野佑二一直怀揣着诗人的浪漫梦想,却难以逃离二战所带来的残酷现实。
安德鲁说,这部小说的英文原名叫《One Morning Like a Bird》,取自日本七世纪诗人柿本人麻吕的一句诗。诗中通过描写丈夫对亡妻的幻觉来诉说哀苦,也暗示了主人公纠结于现实与幻想的精神状态。在另一部小说《乐观主义者》中,经历过卢旺达屠杀的“现实”也成为了撼动主人公精神的直接原因。
对此,安德鲁解释道:“我总是认为,人们在面对战争这种脱离于日常的现实时,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才是最清晰、最具冲击力的。”

复旦教授的274夜环球航行:旅行是一种病,也是药
2023年年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开启一次9个月的环球旅行。

地铁通勤如何塑造了我们的集体生活|荐书
《狐仙崇拜》《至高无上》《通勤梦魇》《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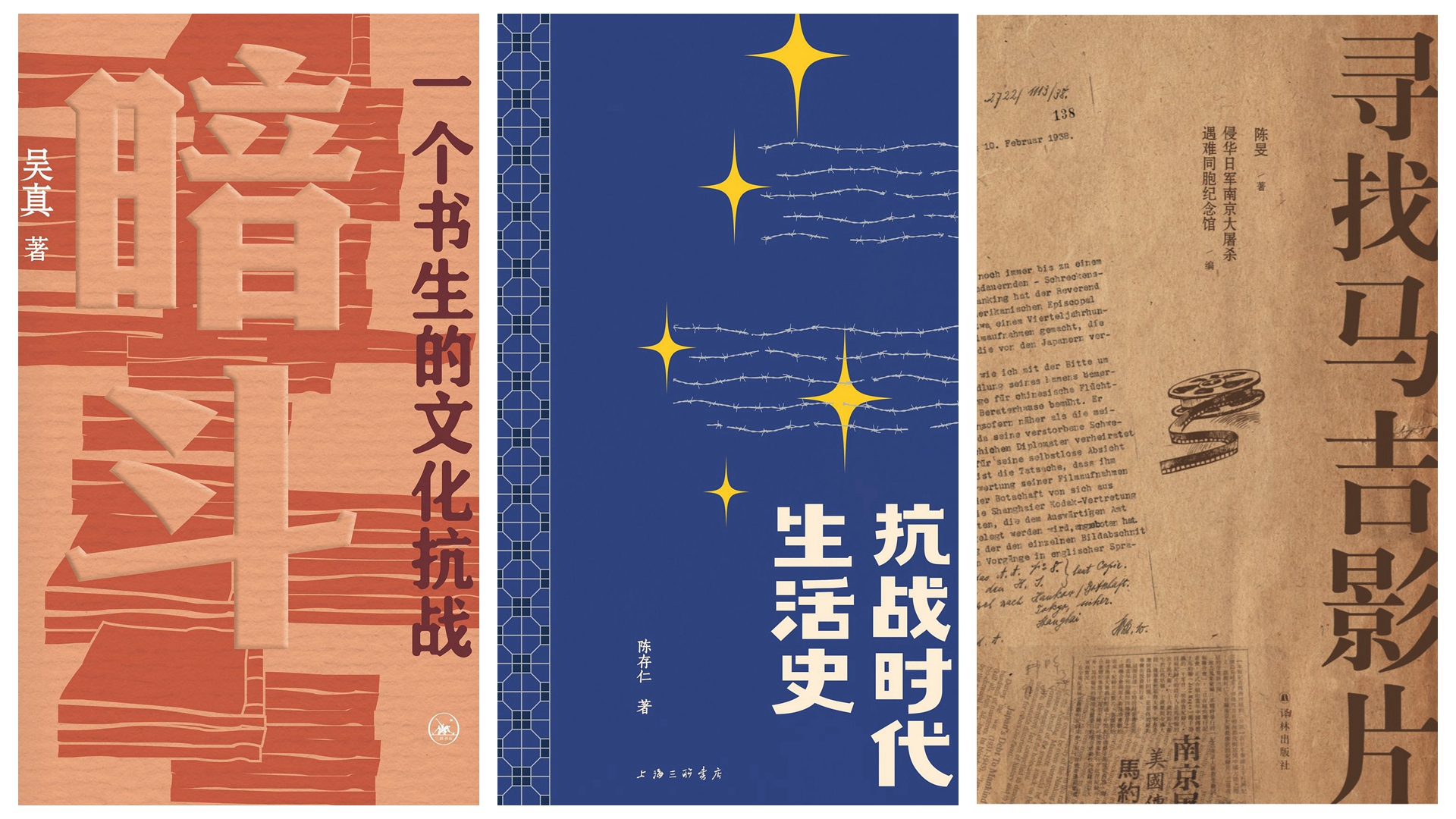
抗战特别书单,跟随这些书回到历史现场
从战事到后方,从部队到民间,一系列新书在此契机出版,帮助我们了解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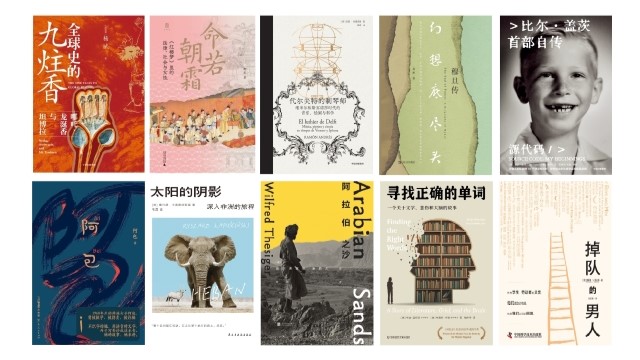
他们坚毅的脸庞闪着光|2025第一财经年中人文图书
“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长期主义、理想主义,需要尊重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基本常识,这些内容在短视频里不可能找到,只能在书籍里。”

上海书展8月13日开幕,阅读活动超过1000场
2025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3日~19日举办。本届书展首次设置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