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冬天的沙溪,行人寥寥,越发显见清旷天地间的生趣,田里的堆肥暖暖下沉,柿子和金色冠状的大树在青瓦矮屋上空静默地有了腾空的气势。小巷里密集的是旧民居改建的客栈,随便向哪个店家打听,这里什么时候是淡季?他们会告诉你,恐怕没有旺季。
即使旅游住宿资源已经饱和,还是有投资者不断涌入,有的把改建客栈当作转手买卖,有的作为生计。经营客栈是向往乡居生活的人解决居住和营生的最为直接的办法。
外来者不断地来,当地人不停想办法,打政策擦边球找地盖新房,像很多生活慢慢便利起来的白族聚居村落那样,相对便捷的交通和信息,改变着城乡时空的距离,各自本原的文化在快速冲淡。
按照建筑师黄印武在《在沙溪阅读时间》中写的——“在四方街通往东寨门的小巷中,就有两个很典型的冰臼,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冰屑和岩屑螺旋打磨石头形成的凹窝,均匀规整”,这些曾存在于冰河纪时期的自然痕迹让人惊叹,但社会文明的演进形式更醒目和杂沓,比之自然的静默,更吸引人的是人的建造历史。上世纪90年代,这个偏僻小镇以其完备的建筑遗存和传统村落形态进入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学者的研究视野。
2003年3月,刚刚从瑞士联邦理工大学完成学业回来的黄印武,加入了“沙溪村落复兴工程”项目,主导设计和实施工作。这一项目由瑞士联邦理工大学主持,世界纪念建筑基金会筹措慈善资金,“试图通过对当地村落文化遗产、生态景观的保护及对古村落和建筑进行保护性修复、改造,辅以基础设施和生态卫生系统的更新,实现对当地村落经济的脱贫和文化的传承,构建一个农村基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黄印武回忆:“开始的四年,针对古村落和公共建筑的保护性修复工作相对紧凑,后来越来越松散了,到2011年断断续续有点事情,做得比较松散。”在村落中心公共建筑遗产的保护和村落建筑修护工作告一段落之后,黄印武选择定居在这里。留在沙溪的原因是,这里亮敞晴朗的天日与温和的气候,说得深了,他无意透露:“留下来,是为了看看它怎么发展。”
隐没在小巷中的一方传统白族小庭院,是黄印武现在的住所,坐西向东的堂屋,延续了旧有的格局和样式,黄印武把原本东南角落的猪圈拆除后,盖了土木结构、南北通透的工作室。
这个原本宁静的小院,也很快被客栈包围。采访的当天,黄印武请来工匠加高一面院墙。“从我来讲,矮矮的墙最有农村特点,屋顶的状态和层次特别好,但隔壁成了客栈,为了遮挡视线就不得不把这堵墙加高一点。”
在乡村蜕变的现实中,不同人群的诉求总是犬牙交错,例如,揣着钱而来的投资者,相中一院老屋,屋主即便有心交易,也会来问问黄印武——“合不合适?”黄印武会反问他:“几十万块钱,就把二三十年的话说尽了么?”他总是这样不断地提醒当地人,再想深一些。
黄印武对民居的本原性价值看得很重,他认为:“打算开客栈的人,按照商业原则行事,往往用最少的钱改建出最多的客房,这样的做法是否符合当地建筑的传统和建筑结构的合理性?”这些问题村民往往没有办法看清,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工价、物价的上涨,村民们拿到的租金实际上难以再盖一个新楼,而旧有的建筑价值又被破坏了。
既能维系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和发展需要,又能平衡观光和投资者诉求的理想的居住形式?这一构想在黄印武的头脑中慢慢成形:“希望联合一些志趣相投的朋友,或者对乡村建设有兴趣的人,以一个村落为试验点,修缮和改造一批民居,让当地人既不搬离原来的房子,生活质量也可以得到提高,而且通过设计,分割出一些相对独立的空间,给愿意来这里度假或短期居住的人。”
沙溪古镇档案
隶属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剑川县,自秦汉以来即为连接汉藏及中原与印度、缅甸等地商业往来的重要关隘,是“茶马古道”上重要的市集和驿站,保留着相对完整的建筑遗存,2001年被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列入当年的世界101个濒危遗址名录。由瑞士联邦理工学院主导的“沙溪复兴工程”始于2002年,旨在以文化遗产保护切入中国乡村可持续发展,2005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负责实施的建筑师黄印武获第二届中国建筑传媒奖。摄影记者/王晓东

从“风险承担者”到“价值共创者”,服务如何重塑万亿平安?

理想汽车NPS再度登顶,诠释何为“价值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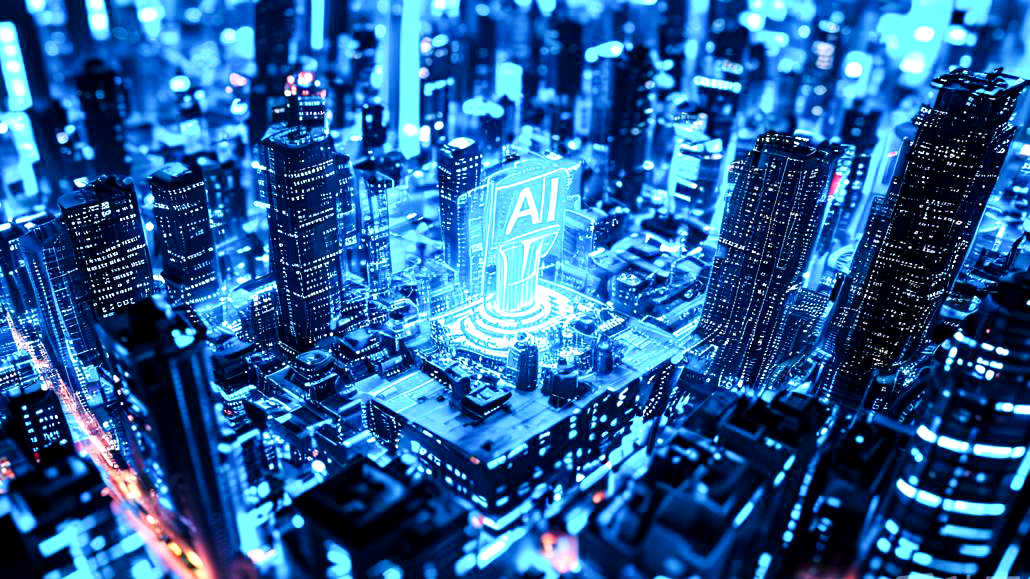
金融大模型迈向价值创造,智能体如何突破“最后一公里”
应对数据安全、算法可靠性等关键挑战。

稀缺、时间与文化:解码茅台的长期价值

大变局下的价值分野与治理重塑:ESG议程与全球秩序的未来
环境、社会与治理(ESG)已从伦理投资演变为全球资本市场核心议程。曾被寄望成为通用商业语言的ESG,在当前多极化世界格局下,未能凝聚全球共识,反而成为不同发展模式、文化价值和治理逻辑冲突的场域。地缘政治紧张加剧,使ESG不再是纯技术或财务框架,而是反映不同文明体对现代化、国家与市场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理解的政治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