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资料图片: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Aat Vervoorn)
“岩穴之士”,是澳大利亚学者文青云(Aat Vervoorn)为其研究中国早期隐逸传统的作品所起的名字。从字面意义看,它体现了多数隐士的特征:居于山林,取法自然。然而,也正是在这点上,中国传统隐士与西方隐士分道扬镳。在中国,隐逸“从一开始就主要是一种世俗的事务,正如隐士的个人完善理想所表明的”。检视其后的逻辑,也能看出中西文化中有趣的差异。
对于写作于20余年前的旧作,文青云表示“很满意”。在他看来,隐逸涉及“个人与社会、政府之关系的研究”,“涉及到在个人的道德信念作为一方,而社会义务和政治职责作为另一方这两者时间可能产生的冲突。”这使得隐逸作为一种行为模式,“轻而易举地穿越两千多年的鸿沟而发出声音,而且在许多方面似乎很现代。”
第一财经日报:你谈到中国古代士人隐逸的原因,“源于一种文化中最高道德权威的个人品行独特理想的实现”,他们对这种理想是否有相对一致的表述?
文青云:隐逸意味着退出政治生活,或许还意味着放弃社会参与,以避免道德层面的自我妥协。隐士的目标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这一目标源于拒绝违背良心、违背自身信念的操守。
古代中国的许多学者及部分统治者均认可这一观点:一个人或许无法真心认同道德正确的标准,但只要他决心坚守自身原则或保持真诚之心,他将同样受到统治者与其他学者的尊重。这一现象尤盛于战国时期,当然了,当时活跃着许多关于个人生活方式的不同理念。这是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因此,一个人应当怎样生活是个众说纷纭、争议不断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许多人都赞同这一观点:见识广博、道德真诚的人应当被允许选择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根据自身信念选择君主。
日报:“道”规范着整个社会,包括君主。对“道”的阐释的不同,是否也影响到隐逸的形式和其在社会中的地位?
文青云:对于正确的道路有着许多不同的理解。儒家学者将道视为先人之路、传统之路、古代圣贤之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必须消极地、不加批判地循道而行。一个人的研究与行为必须与道一致,然而更重要的是根据道的真义行事。孔子曾亲自教导他人:假如为某个国家尽忠必然导致道德层面的自我妥协,那么一个人有责任去效忠另一个国家。这意味着,做正确的事是一种高于效忠任何统治者或国家的责任。同样,道家的老子也说过,治天下的圣人必须认同无处不在的道,但是其他人都必须努力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他们需要强健的身体。)就“循道”而言,老子在某些方面更接近于韩非而不是庄子。
日报:你说隐逸是“社会政治文化核心部位的传统”,能否具体谈谈,隐逸如何作用于社会?
文青云:隐逸要求一个人在不完美的世界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理想生活。因此,隐士成为他人的灵感、楷模与道德权威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表现出了道德勇气以及对崇高行为理想的坚定操守。他们可以成为自己家乡、某个山中隐居之所甚至是皇宫中的模范人物,邂逅隐士之人也得以提升自己的道德操守与理解。静修中的隐士会做些什么,取决于他致力于实现的哲学或宗教理想。有些人转向田园生活或是致力于自给自足;另一些人则在追求道教或佛教目标。鉴于他们均受到过良好教育,许多人会研究并创作散文、诗歌与哲学。文学往往是隐逸的副产品。聪明的统治者也意识到,隐士亦可在政治层面发挥作用。统治者发现,表现出对隐士的尊重并邀请他们到宫中做客,可提高自身道德威望。即使一位隐士拒绝出仕,褒奖其美德也比因抗旨不遵治其死罪更有好处。对隐士以礼相待被视为统治者展示其重视品格、乐于听取贤者意见的仁德之风的一种手段。
当然,诚如鲁迅所言,假如隐士避世不出,完全与世隔绝,他们的影响将微乎其微。但是,似乎很少有人彻底与世隔绝。大部分人会以某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譬如作为农夫、教书先生、僧侣、大夫等等。从某些方面看,或许他们相当于现代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鼓励并组织社区提出倡议,实现自助。作为道德权威,他们可以以有益的方式提供精英文化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接触点。任何高度分层的社会都很有可能在维持凝聚力方面遭遇困难。隐士有助于克服这一难题。
日报:孔子以后的隐逸,越来越触及一个“时”(时机)的问题。对于“时”的考量,除了治与乱、正统与非正统之外,还有哪些考量的维度?
文青云:是的,循环不息的“时”是儒学的关键。我以为,最基本的考量是:“统治者或政府是真心实意地关注民生、维持内部社会和谐与外部和平吗?”当然,这里还存在一个更私人的维度:“假如我接受某个政府职位,我是否能真正有所贡献?是否会有人听取我的建议?”换言之,我们同样需要考虑个人的情况与性格。时机几乎不可能对每个人都有利。
日报:你现在对隐逸的看法,与20年前写作此书时是否有改变?你自己最为欣赏哪些隐士?
文青云:不,我对中国隐逸的看法并无多大改变。我仍然认为,要理解隐逸,必须考虑与隐士相对的政治背景及其隐居生活。有些美国学者会说,只有像陶潜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隐士,在他们看来,其生活是与隐居这一概念相联系的。我的回答是:“那好吧,如果这是你认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不过,这不足以说明,这是隐逸的唯一可能形式。”
然而,陶潜也是我最喜欢的隐士之一。他对儒家和道家的糅合符合我的个性。当然,在他的例子中,还有许多描述隐士生活的佳作。我们应当相信他在作品中透露的一切吗?他的作品是如此出色,以至我们想要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然而,我最欣赏的作品之一却是陶潜写给儿子们的告别信,在信中,他为自己当初的决定——退隐田园,放弃官职,以致家人生活艰辛——而道歉。退世或许的确只是一个个人决定,但它对将要共同承担这一后果的家庭成员亦将产生重大影响。
同样,我比较欣赏梁鸿(东汉),他在诗中表达了隐居生活所带来的怀疑与焦虑。他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实现内心的宁静与圣人般的超脱其实并不如我们想象中那般频繁或容易。对其中许多人来说,实现这种精神上的宁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挣扎。另一个我尤其喜爱的人物是庄遵(严君平)。他仅仅是生活在普通人当中,为他人提供指点与支持,不愿出名,并在闲暇时教习哲学。(罗敏 谭薇 孙行之)
《岩穴之士:中国早期隐逸传统》
作者:【澳】文青云 著 徐克谦 译
出版时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9月

复旦教授的274夜环球航行:旅行是一种病,也是药
2023年年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开启一次9个月的环球旅行。

地铁通勤如何塑造了我们的集体生活|荐书
《狐仙崇拜》《至高无上》《通勤梦魇》《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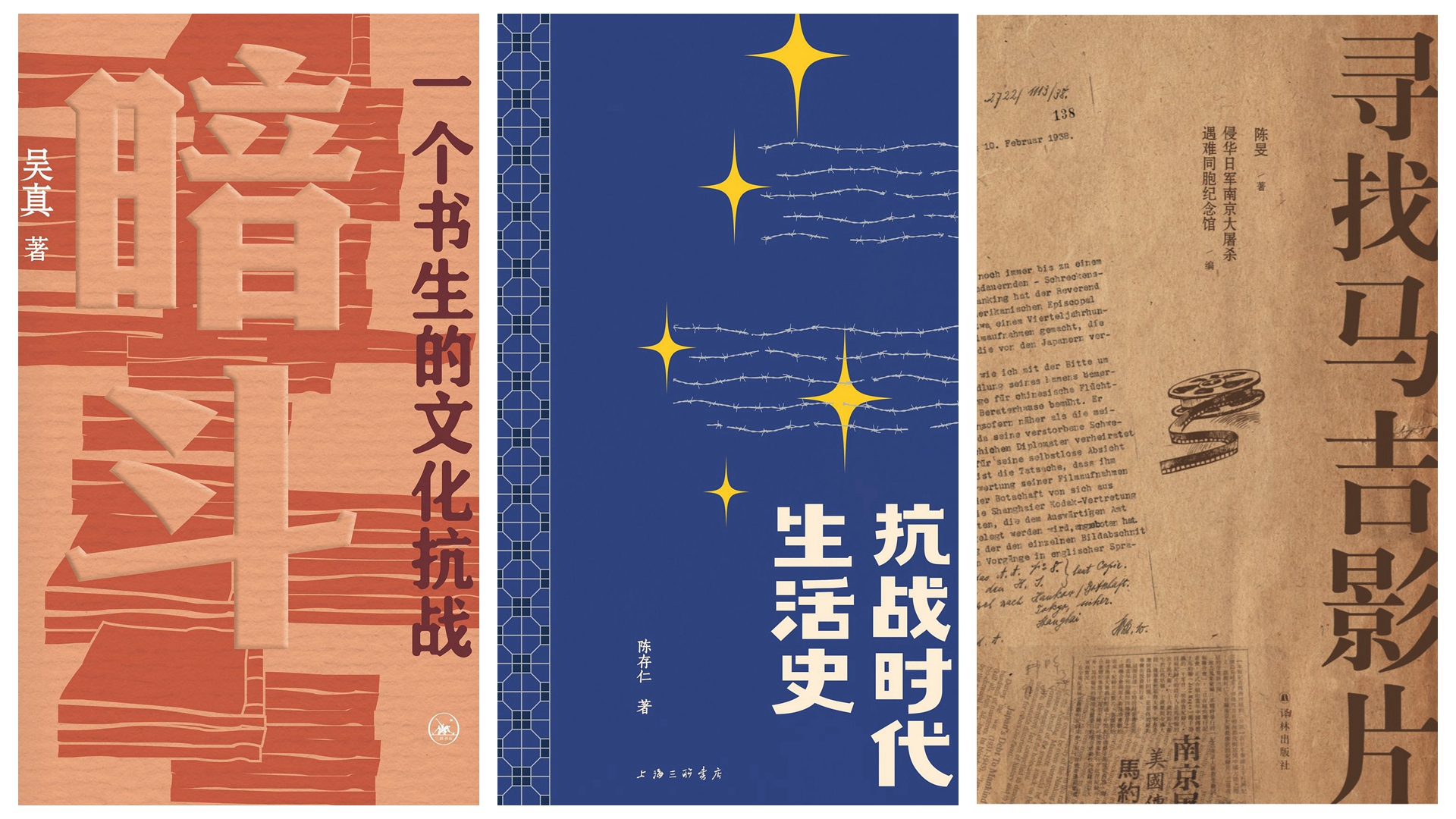
抗战特别书单,跟随这些书回到历史现场
从战事到后方,从部队到民间,一系列新书在此契机出版,帮助我们了解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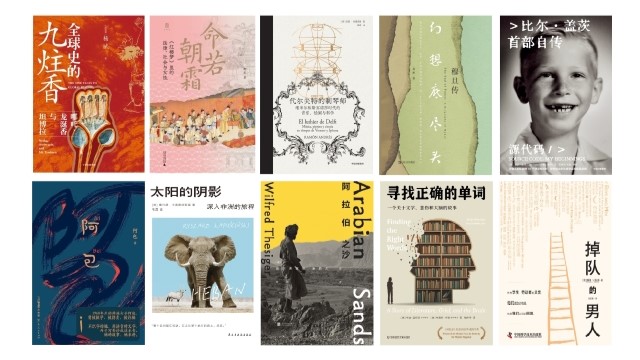
他们坚毅的脸庞闪着光|2025第一财经年中人文图书
“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长期主义、理想主义,需要尊重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基本常识,这些内容在短视频里不可能找到,只能在书籍里。”

上海书展8月13日开幕,阅读活动超过1000场
2025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3日~19日举办。本届书展首次设置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