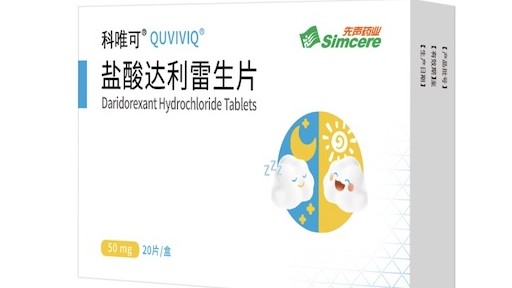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作家毛姆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生活在自己喜爱的环境里,淡泊宁静、与世无争,这难道是糟蹋自己吗?与此相反,做一个著名的外科医生,年薪一万镑,娶一位美丽的妻子,就是成功吗?” 1919年,英国小说家毛姆在他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提出的疑问,至今仍是一句掷地有声的诘问。
近百年来,这部以印象派画家高更的坎坷人生为灵感的小说,被文学和艺术青年奉为圣经。小说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一位过着平静、优渥生活的英国证券交易所经纪人,逃离上流社会,抛妻弃子,追寻自我的精神自由与绘画梦想,最终在贫困潦倒中死于麻风病,留下惊世杰作。今年是毛姆作品进入公共版权的第一年,除了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翻译家傅惟慈先生的译本之外,相继有五、六个出版社推出了《月亮和六便士》的新译本。
9月21日至25日,根据毛姆小说改编的舞台剧《月亮和六便士》将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首演。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香港导演邓伟杰认为,毛姆的作品对于今天生活在大都市的当代人而言,更有切实的意义,“我们生活在大城市,发达地区的人,为了脚下的六便士,往往都会把心中的月亮掩藏,即使得到看似美好的生活,但心中仍是空洞。排演《月亮和六便士》,是一次与毛姆的剧场约会,也是一次和理想的灵魂对话。”
伍尔芙曾说:“读《月亮与六便士》就像一头撞在了高耸的冰山上,令平庸的日常生活彻底解体!”这句话触动了本剧的制作人苏莉茗,她说:“一百年前的欧洲,其实和现在的中国很像,都市文明高度发达,人们好像生活在富足的社会里。但是总有那么一个人会用行动告诉你,生活可以有很多妥协,而理想永远不行。那么,你的理想,你还记得吗?”
寻找精神家园的漂泊者
毛姆笔下的人物形象大都是一批寻找精神家园的漂泊者,斯特里克兰德是这其中走得最彻底的人物。
“小说中的主人公为了追寻精神自由,确实舍弃了很多。他的行为令他身边的人觉得他是无情的,令人讨厌,没有人性的。”邓伟杰说,在现实社会中,也许这样“为梦想而放弃家庭及名利”的极端者并不多,但人们内心总是怀有对精神自由的向往。
斯特里克兰德身在伦敦中上层社会,却是个唯唯诺诺的边缘人,“事事要邀获别人批准,或许是文明人类最根深蒂固的一种天性”。四十岁的他被家庭、事业、社会身份支配,每天与金钱打交道。越是压抑内心对艺术的渴望,爆发出来的欲望就越激烈。
“斯特里克兰德是个无聊的家伙,沉默寡言,对艺术、生活都没有兴趣,一个索然无味的有钱人。”在话剧舞台上,编剧李然通过旁人的口吻,描述了世俗世界里被人们界定的斯特里克兰德。从他离家出走到他客死异乡,所有人对他的解读都是破碎的。而观众却能最清晰地洞悉到,一个渴望寻找灵魂栖息地的人,是如何有勇气去背叛生活,反社会地漠视道德,远离常人所追寻的金钱、喧嚣和享乐,一步步滑向生命的边缘。
李然说,对创作者而言,《月亮和六便士》在文艺青年心中的地位有多高,将原著改编为话剧的难度就有多高。
“《月亮和六便士》是一部优秀的小说,但并不适合直接改成剧本。”李然回忆,他在大学时代就读过这部小说,“当时感触最深的是,一个人要追求最极致的精神自由和自我实现,就意味着他必须与这个世界势不两立。”
“小说的情节是松散的,时空跨度也比较大,甚至议论多于事件。”李然说,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他将功夫花在材料的取舍上,从剧场舞台表演的要求来组织人物行动,甚至略微调整情节,“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的文学美感和犀利精辟的语言风格。”斯特里克兰德从伦敦到巴黎,再到南太平洋的塔希提岛,背弃世俗的伦理和观念,忍受穷困潦倒、疾病缠身,整个经历几乎都由舞台上的旁观者来完成叙述。
“你一点儿也不觉得害臊?所有的人都讨厌你、鄙视你,你都无所谓吗?”在斯特里克兰德背离人伦,抛下妻儿,独自上路时,李然用旁观者的疑惑发出这样的质疑。但观众眼见着主人公经历了从文明走向野蛮,从依顺走向叛逆,从压抑走向自由的心灵演变过程,会逐渐有自己的价值判断。
在话剧《月亮与六便士》中,高更的画作将在舞台上呈现出丰富斑斓而自由的塔希堤岛
天才与世俗、原始与文明的冲突
罗曼罗兰曾说,“《月亮与六便士》呈现出一个小说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美好、艺术和完美。”这个以精辟文字书写的内心世界,该如何呈现于舞台,对创作者而言可谓考验。
“我们会根据主人公在伦敦、巴黎、塔希提岛三个时期的不同心境和绘画技艺,选择并重新组织高更画作中的色彩、笔触等构成元素,结合舞台布景,用多媒体投影等技术加以还原和再创造。”有着二十多年戏剧经验的导演邓伟杰说,色彩和音乐,是他营造戏剧氛围的重要元素。在这个“去戏剧化”的剧本中,如何隐射主人公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用高更的色彩和各种音乐衬托,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从原著到剧本,都有很多讲述和独白,邓伟杰希望用表演、舞美和音乐让这一切活起来。他将伦敦的世俗世界设置成灰色,斯特里克兰德穿着笔挺三件套西服,在华尔兹音乐的舞会上手足无措。物欲横流的伦敦是工整、高雅的,却也如框架般意味着人性的束缚。
到了巴黎,斯特里克兰德独自住在破烂的“比利时旅馆”开始疯狂作画,遁入随意、自如的艺术世界。到了塔希提岛,舞台回归一片空旷,原始荒蛮、神秘迷人的小岛让视觉回归静谧,多媒体将高更的画作投影至观众席,舞台上森林、星空和月亮的出现,意味着斯特里克兰德的灵魂飘升到缥缈的空际。
“总体色调上,我们设计了从灰暗到浓烈的演变,配合剧情,辅助表达斯特里克兰德的心路历程。”邓伟杰说,在斯特里克兰德的造型上,从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演变至临终前衣衫褴褛、满头包裹着肮脏的纱布,让观众直观地看到天才与世俗、灵与肉、原始与文明的冲突。
“毛姆其实呈现了从‘六便士’到‘月亮’的过程,但是如何取舍,如何判断,他并不告诉我们答案。同样,我们也希望能够激发观众的思考。”编剧李然相信,尽管《月亮与六便士》具有极大的知名度,但也会有完全没看过原著的观众走进剧场,事实上,他们更期待这样的观众,能在话剧中获得启示和自我感悟,理解一位漂泊者在经历了空虚疏离的前半生后,为什么要去追求心中的艺术和自由的“明月”。
邓伟杰笑称这其实也是一场“月亮和六便士”式的旅程。在热钱涌动的演出市场,能有这样一个团队站在舞台上,和观众们一起经历一场理想的灵魂对话,实为不易。邓伟杰希望,走进剧场的观众可以在月亮中看见理想的光芒,“尽管现在谁也不知道,毛姆也不知道,月亮究竟是如何出现在舞台上的。”
问邓伟杰,如果毛姆真的坐在台下看这出话剧会如何想,他对第一财经笑答:“他可能会说,你们既然懂得我所写的,为什么还不去追寻?”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