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决定拍摄《敦刻尔克》前,英国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一直自我怀疑,“到底要不要拍这样一部电影,把它用这样一个本质上是娱乐性的形式来展现出来?”
直到电影在全球上映,诺兰才在大银幕上给出自己的答案——《敦刻尔克》的镜头里没有血腥杀戮和密集炮火,甚至没有完整故事和真正意义上的主角。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退到背后,观众能感受到的,是人类在极端情境下的求生意志。
敦刻尔克是二战史上最悲壮也最著名的一次大撤退。1940年5月,德军以闪电战的方式席卷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南部,盟军被一步步逼至绝境。5月25日,40多万士兵被逼退到法国敦刻尔克海岸,进退两难,唯一的生路是横渡面前的汪洋大海。5月26日,“发电机行动”指令下达,40万人命悬一线,等待救援。
十天后,33.8万名士兵撤回英国。6月4日,丘吉尔通过全国广播宣告了这个奇迹:“我们将在海滩上战斗,在陆地上战斗,在田野中战斗,在街巷里战斗,在山峦中战斗,我们永远不会屈服……”荡气回肠的鼓动演说中,敦刻尔克撤退被描述成一次壮举,死里逃生的军人为欧洲反法西斯战斗保留了有生力量。
敦刻尔克撤退是一场奇迹,但归根结底并非胜利。它集合了二战史上扭转战局的关键事件、共同灾难、民族创痛、家国情怀等等各种标签于一身。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战争题材,无论还原到什么程度,终究只是真相的一部分。作为导演,诺兰该如何以审慎态度介入这段沉重历史,如何铺陈细节,在想象的基础上增添戏剧效果?
沉浸式的逃生体验
诺兰曾在《盗梦空间》中制造出几重梦境的浮华特效,又在《星际穿越》中营造多维时空,但在《敦刻尔克》里,擅长视觉的他控制了对奇观的展示。
叙事空间被压缩至极简。全片零星对白,像是回溯默片时代,紧张的音乐如同机械钟表声、警笛声、齿轮声,从头至尾填满影片。他用晃动的镜头、灰冷的色调、交错的片断,让你感受到人的绝望与希望如何交织。不堪忍受的观众认为,这种体验无异于酷刑。
诺兰用电影表达自己的的态度:比起真正的英雄主义,尊重人类在生死抉择中的原始本能,或许才是战争中最真实的东西,有时仅仅靠人类本能的合力也能够成就一项壮举。他说,“这是一个关于撤离的故事,我把它当成一个关于逃离的悬疑电影来拍,而不是战争片。”
1995年,诺兰夫妇驾着一艘小帆船,从英国出发,历经19个小时,终于渡过英吉利海峡,抵达敦刻尔克。没有突袭的燃烧弹和神出鬼没的鱼雷,他们面对的唯一敌人,是海上的狂风与巨浪。
在搜集素材的过程中,诺兰走访了一些经历过敦刻尔克撤退的老兵。他们向诺兰回忆了很多细节的感官体验,当时身处的环境,水、海滩、炮弹的声音。在电影中,诺兰最想做到的,就是让观众感受到老兵们的回忆,身临其境地回到1940年的敦刻尔克现场。
通过急剧压缩的时空,诺兰为观众营造出沉浸式的逃生体验。他通过代入感极强的三组不同维度的参与者视角,让观众跟随者士兵的视觉与听觉,在时间流逝中感知恐惧,在旋转的天际线中迷失、晕眩,时刻做好准备躲避呼啸着俯冲的德国战机和从天而降燃烧弹。
诺兰甚至做到了李安在《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中没能完美实现的一种真实感。
从影片的第一秒开始,观众就参与了逃亡。六个士兵在荒无人烟的街道上跌跌撞撞,传单像秋叶在脚边打转,有人凑在裸露的皮水管中喝水,有人用拳头砸开窗户找桌上的烟抽。突然一阵乱枪,士兵们开始仓皇逃窜,镜头紧紧跟随,空旷的街道突然被急促的脚步声和子弹爆破声充斥。他们一个接一个倒下。紧张、恐惧、毛骨悚然,只有一个人逃了出来,冲到几百米外的海滩,海滩上成千上万的士兵如同蝼蚁,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真实的历史中,德军前线并没有如此逼近敦刻尔克的海滩,而是在10英里之外。通过士兵几百米的冲刺,诺兰裁剪了距离,从而制造出压迫式的危机感。到此为止,没有一句台词,你只看到惊恐万分的双眸,紧张僵硬的肢体动作,蜷成一团抖动的双肩,而音效则如幽灵一般,压制着观众焦虑的心脏。
每一分每一秒,诺兰都在把他最擅长的时空拼接巧妙运用,时间被重组,悬疑感因而增强。空中战机的追逐战、海上的民间救援、陆地上等待撤退的士兵,三条线索散落在不同的时空,营造出⼀种无处可逃的恐惧氛围。诺兰想要传递的,是着恐惧中藏着的人性微光。
除了电影末尾出现的两个持枪的面目模糊的士兵,诺兰的镜头中从未出现过德军攻击的画面。他认为,电影的责任是避免带有误导倾向地展现纳粹形象。
真正的英雄被遗忘
《敦刻尔克》里没有真正的主角。飞行员的英雄主义、民间救援的平凡与伟大、大撤退的绝望惨烈,在天空、海洋、陆地三个时空相互交错。
有时,你看到一些人的几分钟或几个镜头,仿佛就看到他们的一生。他们仓皇进入一场未知命运的战争,本能反应是寻找活下来的机会。就像电影宣传语所说的,活着就是胜利。
在一场溃败后的撤退中,诺兰找到了叙述胜利的方法,三条叙事线的重叠,一步步将影片推向高潮,实现了一次艰难的胜利营救。
然而,标准意义上的胜利并不存在。历史虽将敦刻尔克撤退称为胜利,但只有亲历者自己清楚经历了什么。拼死逃生的战友随波浮沉,正如影片中曾救出英军的法国军人再也逃不出战场。
电影没有大段表现法国人的绝望,但片段中也隐晦地涉及,例如法军士兵扒掉阵亡英军士兵的服装冒充英军混上救援船,在栈桥上恳请英军军官放行的法军士兵却仍然遭到拒绝,英国士兵在通过法军守卫的街巷时,与法军士兵有短暂的眼神交流,双方都十分冷淡。电影并没有回避,法军与英军同为盟友,在面临撤退时的微妙情绪。
提到敦刻尔克战役,很多人都会提及希特勒的昏招,命令已经处于绝对优势的德军装甲部队停止前进,磨蹭了三天才恢复攻击。但德军对敦刻尔克前线盟军始终保持高压,十多天里,德国空军和海军一直在使用多种手段杀伤在海滩上等待救援的英法联军。
影片中,英国空军的喷火战斗机编队与德国空军争夺制空权,一路上,三架战斗机与德国空军多次遭遇,最后或被击落,或遭迫降,没有一架返航英国。影片末尾,一位幸存的英国飞行员回国后遭遇一名陆军士兵的抱怨,救援的时候,空军在哪里?在这场大撤退中,一些真正的英雄被遗忘了。
为了护卫从法国敦刻尔克到英国多佛短短21英里的航程,英国空军每天要出动300架次的战斗机在海峡上空来回地穿梭,他们要跟德军的轰炸机作战,防止它们炸沉正运送兵员回国的船只,保护海峡中漂流的各种民间小船。影片中,汤姆·哈迪饰演的空军法瑞尔为了尽力掩护地面的战友,放弃返航,用尽最后一滴油,击落一架轰炸机,自己却迫降在德军占领的海滩,最后被俘。1940 年6月4日,最后一艘救援船从海岸离开时,仍有4万名盟军留了下来,在敦刻尔克附近的阻击阵地上遭德军俘虏,一部分人被当场处决,幸存下来的则受虐直至战争结束。
战争在人类历史上从未停歇,无论是源于种族的仇恨,利益的纷争,甚至戴上自由、道德的面具,它最终都是一场普通人消灭普通人的悲剧。
海滩上的人坚持对抗绝望活下去、空中的飞行员坚持护航到燃油耗尽、海上的普通船主坚持驶向敦刻尔克,活下来的人都拼尽了全力。或许,最后普通士兵朗读丘吉尔的那段演讲可以被视作隐晦的反讽。这群经历了生死考验的军人再次站在田间,站在海上,站在天空的时候,是否还能够视死如归呢?
法瑞尔是个英雄,但他没能回到家乡。《敦刻尔克》和《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用了截然不同的叙事方式,风格迥异,却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一起。两部电影有一句非常相似的台词,一个是带我回家,一个是带我回安全的地方,回到战场。看似截然不同的选择,其背后,都是战争对于人性的摧残。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特朗普称已停止所有解除针对伊朗制裁的工作
特朗普称已停止所有解除针对伊朗制裁的工作

避险热度短暂熄火,黄金凭何稳坐中长期投资 “C 位”?
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全球不确定性因素、美联储货币政策走向,以及美元国际储备地位的变化,仍是黄金价格运行的主导逻辑。在美元信用逐渐走弱的大环境下,黄金凭借其独特的避险和保值属性,依旧是资产配置的重要选项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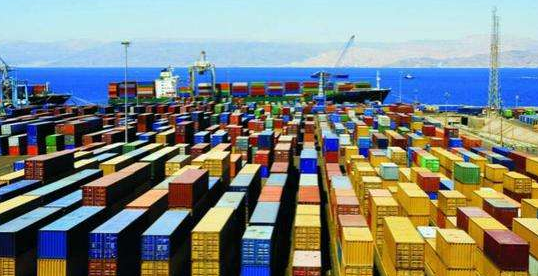
以伊宣布停火:国际航运仍忧喜交织,外贸企业抓紧发货
昨天还在担心以色列客户没有按计划提货的中国外贸人,正在抓紧联系对方,尽快发货。

中资企业聚集法国“电池谷”,敦刻尔克港将持续扩容
敦刻尔克地区的海上风电场、光伏设施建设、绿色氢气生产和合成燃料生产等一系列项目正在加速筹备中。

从信息化战争到智能化战争,未来战争或将经历深远变革
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无人装备(包括俄乌战场已经参战的无人舰艇、无人车等)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可以大幅减少伤亡而被运用,而是有着关乎战争胜负全局的根本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