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如果没有亲自观看影视剧或者阅读书籍,只是满足于那种“三分钟”的解说版,你会错过什么?
打开视频网站或者听书平台,经常能看到那种“三分钟读完一本书,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的解说栏目。这些内容能让你快速地了解一部作品的主要故事情节,掌握一些流行文化和社交谈资。
但是,这些解说版,抹除了原作里两种非常重要的要素,那就是“细节”和“讲述者”,没有了这些,故事就只是记载、资料和数据,不能让你完整地感受原作最美妙、最神奇、最浪漫的体验。
其实我一直在倡导一个理念,那就是:要想更好地去体验原作的魅力,就要去“亲自阅读,亲自思考”。
故事发展到今天,似乎又再次回到了“口述故事”和“图像故事”。
大家想想,电影是不是就是运用“图像”来进行叙事的一种终极手段呢?
而有声书就是另一种高级形态的口述故事。现代人太忙了,忙到时间都变成了碎片,因此远古时代的口述故事在科技发达的2021年,成为了利用碎片时间的最佳方式之一。开车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愿意听一听这些口述的故事。
当然了,这是一种非常浅显的说法。我只是想说明,当现代科技丰富了故事传播的方式,让人们习惯了观赏画面,习惯了聆听之后,阅读似乎就被疏远了。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说,太长不看。我特别不喜欢这四个字,因为它催生出了一种非常可怕的故事形态:
打开视频网站,或者听书平台,输入“3分钟”“5分钟”这样的关键词,我们将看到一种很奇特、但又很受欢迎的故事形态:用很短的时间讲述一个很长的故事。三分钟带你读完一本书,五分钟看完一部电影。这些视频的制作者很有本事,不论是多厚的书,多长的电影,似乎都能在几分钟内给观众们讲清楚。
难怪有人说,如今的时代俄国小说肯定是不吃香了,因为人们没有时间听作者啰啰嗦嗦地讲几十页落寞贵族的日常生活,我们就想知道,安娜卡列尼娜和沃伦斯基最后到底有没有在一起?林黛玉到底死了没有?哈利波特有没有战胜伏地魔?人们急于得出一个结论,并且是短时间内得出一个结论。三分钟故事就是看准了现代人的这种心理,顺应了现代人的这种需求。
那么,这样的三分钟故事,到底行不行呢?我说,不行。我甚至要说,这是最糟糕的读故事的方式。
三分钟故事到底有什么问题?它对故事本身,对我身后这些伟大的讲故事的人,到底做了什么?
去年我和湛庐合作,翻译了一套英国作家斯蒂芬·弗莱的作品《神话》以及《英雄》,目前这套三部曲作品的最后一部《特洛伊》也正在翻译进行中。这套作品是斯蒂芬·弗莱对希腊神话的重述。当时在翻译这套作品的时候我就想,是什么让它脱颖而出,和从前我读过的希腊神话都不一样?它打动我的部分究竟在哪里?
首先我想说的关键词是:具体
斯蒂芬·弗莱所重述的希腊神话,就是一个又一个非常具体的故事。这个具体并不是说它长,而是说它拥有丰富的细节:天神们的早餐桌上摆着的是花蜜酒,而穷苦的老妇人招待客人的只有无花果干;英雄和朋友聚会时玩的是掷铁饼,在比赛中获胜的运动员拿到手的奖品是棕榈叶或者橄榄枝。除了这些生活细节,他还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风景。通过他的描写,我们能看到城堡上飘扬的旗帜和闪着微光的城墙,能看到城邦里热闹非凡的集市和城邦外尘土飞扬的竞技场。
除了场景方面的细节,弗莱还用细节来塑造人物。身为戏剧家,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想象力,能为每个角色设计出栩栩如生的表情、动作、言语……宙斯的好色,赫拉的嫉妒,赫尔墨斯的狡猾,阿瑞斯的鲁莽,这些本来很平面、很脸谱化的天神,在弗莱的笔下变得立体了。
他所描绘的场景,就像是曾经真实发生过的生活片段,他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就是近距离地看希腊诸神和英雄们的生活。
具体的细节能够成就一个好的故事。没有了这些,故事只是记载,只是资料,只是数据。
具体的故事不但能重现栩栩如生的场景。它还有更重要的作用,那就是能够重现情感。
最初,人们产生了讲故事的渴望,试图记录下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更渴望记录下来当时所产生的某种奇妙的东西,那就是情感体验。情感是抽象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除了当事人,甚至都很难说明它曾经发生过。但是情感对人类来说又是那么重要。甚至可以说,我们所做的一切,只不过都是为了换取某种情感体验。
只有故事能够传递这些珍贵的情感。具体的、丰富的、充满细节的故事,为所有微妙的,暧昧的、抽象的情感表达找到了出口。
所以,让我们回到三分钟故事的思考中来。三分钟故事的短,就要求它必须剥离细节,必须浓缩,必须概括。也就是说,它让一个具体的故事,再次变回了一个结论,一段资料,一份数据。它把故事抽干了,故事“具体”的本质在这样的“缩写”中消亡了。
有人会说,也许这样的三分钟故事是想做一个引子呀,虽然我“缩写”了,但我把精华提炼了呀。如果我的目的是让你对这本书感兴趣呢?听过我提炼出来的精华,对这本书产生兴趣,然后再去读书,补充细节,不也是功德一件吗?
真的是这样的吗?那就让我们聊一下第二个关键词:讲述者。
在英文里,故事可以用不同的词来表达。其中一个是我觉得最妙的,那就是story telling。Tell就是讲述,后面加上ing,就是进行时。这个telling加得很有意味,它把“故事”从一个似乎静止不动的“物体”,变成了一个动作,一个带有意愿的动作,突显出的是故事背后“讲述”这个动作的发出者。
还是回到斯蒂芬·弗莱的《神话》。我本人是神话爱好者,读过许多版本的希腊神话、北欧神话、中国神话。然后我发现,有一种类型的神话写作,给我一种读资料的感觉。时间有了,地点有了,人物有了,主要的事件也有了,但是读起来,怎么感觉像在档案馆里读卷宗,不是故事。因为你从它的背后,感觉不到讲述者的存在。它很中性,很疏离,很冷。
但是斯蒂芬·弗莱在重述神话的时候,他作为讲述者是很有存在感的。在他的讲述中,读者能感受到他的幽默风趣,看到他对天神们细腻独到的理解,领悟到他对希腊神话深刻的洞见。
故事必须包含讲述者。讲述者必须以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在讲述里,有的时候是讲述的方式,我们称之为“文笔”或者“文风”;有的时候是讲述的角度,我们称之为“立场”。面目模糊的讲述者,讲出来的故事面目也必定模糊不清。好的讲述者都是鲜明的、活泼的、有温度的,为什么那些口耳相传、作者不详的伟大故事,只有到了荷马、欧里庇德斯、莎士比亚这些讲述者的手里,才真正地发光发热?因为是讲述者投入的生命之火给了故事鲜活的力量。
我们常说,一百个观众心里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这是怎么做到的?是因为讲述者隐身了,所以观众可以随心所欲地去理解哈姆雷特吗?
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莎士比亚投入了巨大的个人能量,哈姆雷特才成为这样一个能带来一百种、甚至一千种解读的经典角色。莎士比亚将流传在印欧地区的哈姆雷特式的传奇元素收集起来,加入了他对人生、对死亡、对复仇、对爱恨的理解,才最终成就了这样一个复杂、深刻的故事。是讲述者在故事中施了魔法,故事才能变成一个活的宇宙。
所以再回到三分钟故事的问题上。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抹杀了讲述者,他们撤销了魔法。在三分钟故事里,我们遇到的讲述者不再是莎士比亚、钱钟书、曹雪芹,而是那个视频的制作者。他用自己的理解,自己的看法,自己的体验,代替了讲述者的体验,也代替了你的体验。
一个失去了具体性,讲述者也遭到抹杀的故事,还是原来的那个故事吗?
他们说世界变得越来越便捷,越来越忙碌,可在我看来,这个世界是在变得越来越抽象。丰富和具体在消失,复杂在消失,暧昧在消失,三分钟故事所背离的,是阅读的本质。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去阅读一个故事呢?
其实我前面已经说了很多,所以我要给的建议真的十分简单。那就是,
亲自读,亲自想。
只有亲自读,你才能找回那种完整的阅读体验,才能亲手触摸到讲述者构建的那个神秘宇宙中每个细微的角落,才能在这个旅程中找到始于文本,但却大于文本的感受。
故事最美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复杂和暧昧。复杂和暧昧就意味着,惊喜可能藏在每一个角落。
好的故事构建起来的宇宙,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探索,因为它让我们得到了窥探另一种可能性的机会,得到了获取新的体验的机会。这场旅程,你必须亲自走。爱一个人,我们不希望别人代劳;吃一顿美食,我们更愿意自己来享受,阅读一个好故事这种世间最美妙、最神奇、最浪漫的体验,又怎么可以假手他人呢?
阅读一个故事,等于是和讲述者进行一场只属于你和他的心灵碰撞。只有当读故事的你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结合属于你的真实生活来体验和共情,才算是真正完成了这一场跨越时空的与讲述者的碰撞。只有亲自去想,才不会让一个精彩的故事沦为一场娱乐;只有亲自去想,才能从别人的故事中,找到属于你生命的养料,拥有审视和思索的力量。
(本文选自黄天怡演讲;转载自湛庐阅读App韩焱精选栏目,韩焱为湛庐创始人)

文章作者

复旦教授的274夜环球航行:旅行是一种病,也是药
2023年年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开启一次9个月的环球旅行。

地铁通勤如何塑造了我们的集体生活|荐书
《狐仙崇拜》《至高无上》《通勤梦魇》《与希罗多德一起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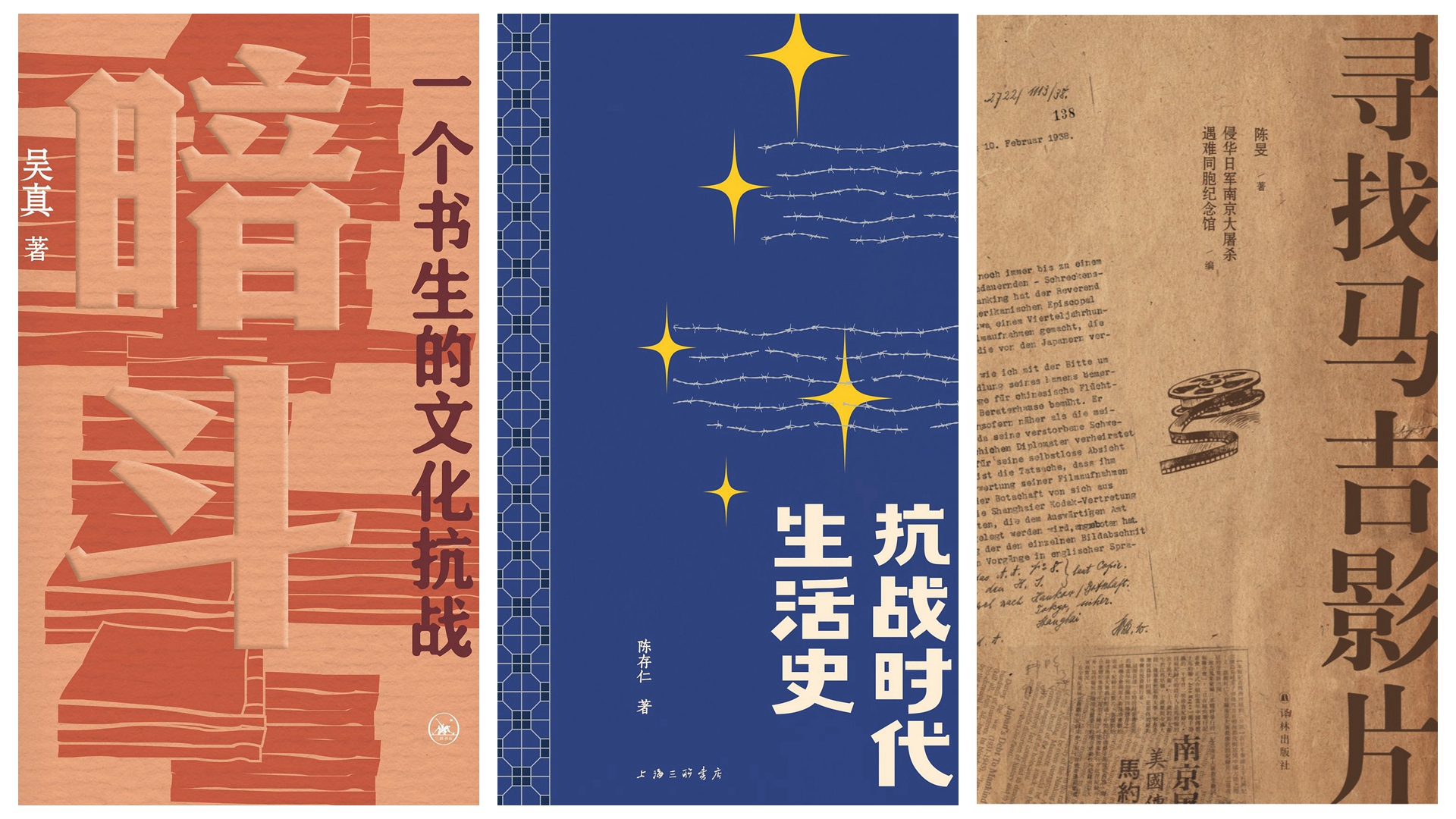
抗战特别书单,跟随这些书回到历史现场
从战事到后方,从部队到民间,一系列新书在此契机出版,帮助我们了解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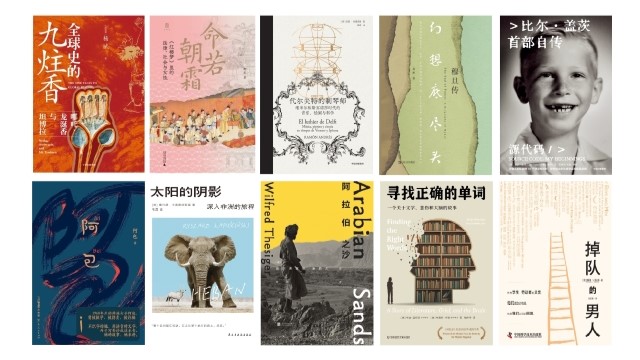
他们坚毅的脸庞闪着光|2025第一财经年中人文图书
“我们的社会非常需要长期主义、理想主义,需要尊重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和基本常识,这些内容在短视频里不可能找到,只能在书籍里。”

上海书展8月13日开幕,阅读活动超过1000场
2025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3日~19日举办。本届书展首次设置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双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