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由于一些不清楚的原因,一种陌生的传染病在某个亚洲城市暴发,随即在一个相互联系的跨国网络中迅速蔓延,所到之处,接连出现几波流行高潮,成为一种全球性疫病。各国政府和科研机构都在研究其成因,但迟迟无法达成共识,对这种传染病的认识在仓促间远远谈不上清晰统一。这就引发了世人广泛的忧虑与恐慌,连伦敦的医生和作家都不禁恐惧:英国文明是否会毁灭?国家会走向堕落吗?
是不是看起来很像我们当下所经历的新冠肺炎疫情?但这其实是19世纪中叶的霍乱大流行,英语里在1830年代甚至专门出现了“霍乱恐慌”一词。霍乱最初只在印度的局部地区流行,但一个交通、信息等世界性网络已逐渐成形的时代让人陷入矛盾的境地:它既给了人们空前的自信,也使他们陷入空前的脆弱,因为正是借助这样的网络,霍乱等传染病乃至由此而来的恐慌情绪,才能迅速传遍全世界。
那是一个帝国的时代,少数列强瓜分并支配了全世界。与现在边界清晰的民族国家不同,帝国是一种更零散、多样且不同质的结构,往往是在矛盾中整合、区分,这就使得要执行一种标准化的管理体系变得加倍困难,而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原本不对等的地位,在疾病流行之下也被动摇了:尽管直到1832年,巴黎人仍然傲慢地认为霍乱这样“落后的疾病”源于亚洲脏乱的卫生环境,不可能在这个世界的“文明中心”暴发,但现实是它无差别地袭击了西方几乎所有主要城市。

所谓“恐慌帝国”,指的就是在面临全球疫病流行之际,这样一个跨国网络如何作出反应,由此引发的恐慌又如何暴露一个国家管理体系的缺陷,也正因为这样空前的危机显示原有的规则已难以应对,新的临时性政策才随之创制出来。换言之,在此聚焦的与其说是传染病本身,不如说是人们如何应对传染病。
当一种陌生的疫情在人群中爆发时,恐慌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愚昧落后,而是人们在面对一种自身不熟悉的巨大风险时所涌现出来的本能反应,直到现代仍是如此。1995年,埃博拉病毒在西非暴发,在当地引发巨大恐慌,因为一旦感染就会迅速死亡,但感染原因不明,似乎没有人对它有免疫能力,除了最原始的隔绝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阻止其蔓延。如果说现代社会有什么不一样,那就是疾病传播的网络,也是一个信息流通的网络,因而这种恐慌可以在媒体上得以迅速传播。
看似矛盾的是,“恐慌”正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出现。在真正落后的农业时代,不仅病毒很难传播开来,恐慌情绪也一样;只有当现代化将不同的村镇、城市、国家连接成为一个高度关联的统一体时,任何重要的变动才会迅速传导开来,当失衡超过临界点时就会出现恐慌。在美国,表示经济萧条开端的“恐慌”,是直到1880年代这个“镀金时代”才出现的现象。
并非偶然的是,正是由于当时的城市无法有效预防和管理黄热病和霍乱,美国才催生了国家卫生局(1879年)——这有史以来首次使美国作为一个国家而非分散的各州、各城市与流行病做斗争,并创造了一种后来被美国公共卫生署沿用的模式,那就是独立于各地的利益,收集并公开疫情相关数据,通过积极的协调合作,决定适当的检疫措施,尽快使社会恢复平衡。
既要确保国际网络中人员、资金的流动性,又要控制疫情、恐慌的蔓延,这对一个社会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恐慌帝国》一书的重要主题,就在于当公共突发事件爆发时,现有的资源、技术、理念不足以应对来自社会、政治、环境和生物各方面的挑战,一个国家管理体系的缺陷暴露出来,此时就往往需要制定临时性政策。一旦这种临时举措被证明为有效,得以保留下来,后续就成为“新常态”。
从1894年暴发于香港的鼠疫来看,传染病在无意中充当了“试纸”的作用。鼠疫既是一个等待人们发现探索的对象,也是一次“能够阐明社会价值与制度实践基本模式”的自然实验。这一点,一次次被历史所证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社会运行机制获得了“免疫”能力自我更新,最终达到更健康的新状态。
在新模式尚未确立之前,注定是充满争议乃至混乱的,因为人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应对它。1832年纽约霍乱大流行,市政当局试图通过故意低报死亡率来淡化大众对疾病的恐惧,与此同时,也利用恐慌来改变大众的行为和敏感度。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霍乱流行的紧急事态的授权下,“常态行为违法化”旨在清理“那些麻烦的人或事物”,以支持国家对公共卫生的干预。
疫情引发的恐慌,对当时的排外情绪更是推波助澜,因为霍乱被认为是“不文明”的低劣种族带来的。法国人建议干脆封锁整个中东边界,阻止他们进入欧洲,连当时英国的社会名流都说:“肮脏的异教大军连同他们被感染的褴褛衣衫、毛发皮肤,每年都到维也纳、伦敦或华盛顿屠杀成千上万天资聪颖、容貌俊俏的吾辈中人。”纽约市长休·格兰特在1892年致函哈里森总统说:“我们必须阻止更多移民来到这个国家,直到人们对霍乱进入国门的恐慌结束为止。”《纽约时报》也对此表示赞同,认为移民对美国的卫生状况构成威胁,“我们必须记住,霍乱正是源自下等人的住所”。
当时全世界虽然已经连成了一个网络,但一体化程度还很低,检疫的随意性法律框架,意味着对传染病的应对还远未标准化。举例来说,在1830年代,一艘从君士坦丁堡出发的船只在马赛要被隔离60天,但在威尼斯只须被隔离34天。许多人认为检疫实践的差异导致检疫效率低下甚至无用,对防疫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各地各搞一套的做法,也大多没什么科学依据可言。英国医生、法学家和探险家阿瑟·托德·霍尔罗伊德断言,海港检疫“根本没有科学理论支撑,检疫实践充满矛盾,荒谬无比,祸害无穷,都是出于无知或私利”。
也正是这种不协调,最终促使各国鼎力合作,1851年在巴黎召开第一届国际卫生大会,在地中海地区有相关利益的12个国家各派出两名代表:一名医生和一名外交官。这显示出防疫对各国而言,从一开始就不单是一项医学措施,因为医生“代表科学元素”,而外交官则旨在捍卫“海事行政管理的商业利益”。这种不同专业背景人员的组织结构,既显示了会议缺乏预先协议作为指导和规范,也表明人们对防疫有着诸多方面的不同关切。无论如何,这是公共卫生国际化的重要时刻,正是这次大会,催生出了后来的国际卫生组织(WHO)。
当然,历史的教训并不能照搬,如果文献记载没有欺骗我们,19世纪那些陷入“霍乱恐慌”的欧美人,似乎比他们的后代更容易陷入恐慌,但这又是为什么?这还不止是对传染病如此:1750年2月8日和3月8日,伦敦遭受了两次轻微地震,无人死亡,但地震日期的重合引起市民的极大恐慌,一位精神失常的军人到处发布预言,宣称第三次地震将于4月8日发生,并摧毁一切。当然,这并未发生,但当时确有很多人相信。这与其说是当时的人们愚昧轻信,不如说是因为在近代早期,人们缺乏公开、透明又可信的信息充分供给,加上抵御风险的能力很低,一旦遭遇什么事就更容易做出过度反应。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曾说过,到了近代,人类从原本由神灵主宰的“命运社会”转向一个专家主宰的“风险社会”,这伴随着原本天命之类宗教观念的衰落,每个人不论是否愿意,都只能学会面对风险、理性判断,进而掌控自己的命运。贝克在《风险社会学》中断言:“风险社会标志着一个在日常感知和思考中推测时代的黎明。人们总是就相互矛盾的对现实的诠释而争论着。”
对每个现代人来说,这都是艰难的一课,因为这意味着已经没有神灵可以依靠,在“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只能面对不可控制又层出不穷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包括全球疫病大流行在内)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现代化的产物。这意味着现代的自我必须对应于这个具有新的不确定性、差异性和断裂性的风险社会,被迫做出艰难的调整。
棘手的一点是:此时原本最需要个体的理性,但正如美国传播学家李普曼所言:“一旦恐慌情绪蔓延开来,理性就根本派不上建设性的用场,很快,任何一种秩序似乎都比无序更受欢迎。”换言之,当人们在面对恐慌时,软弱的个体往往寻求更强大集体的保护。正如《恐慌帝国》中所指出的,“当我们审视两个世纪以来的恐慌,我们应该吸取的最核心教训是:如果我们希望改变剧本,我们就必须一路追剧到最后,学会判断何为利用恐慌,何为滥用恐慌”。
对近代东亚而言,伴随着传染病防治技术引入的“卫生”话语,原本就是一种西方理念。阿部安成在回顾转折期的日本近代国家与卫生时指出,当时日本社会所重视的并不停留在个体层次,还涉及到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尤其重要的是不让疾病传染给他人,“将个人的身体健康、安全与全体国民与国家的安宁、富强相连接,把传染病蔓延的恐慌下的人心凝聚在一起”,由此,“集合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由此而获致的幸福就与日本的富强和幸福联系起来了,给作为‘国民’的能动体注入更大的活力,就会使之成为权力秩序”。借由预防传染病的公共卫生举措,一个“国民”共同体得以锻造成型,但对病弱、不洁、不卫生的歧视也深深影响了日本的社会心态,“如此一来,人的身体、心性和生活被重重束缚的近代来临了”。
正如我们当下所见,不同国家应对全球疫情远不止一条道路,甚至恐慌程度、对风险的判断也千差万别,但无论如何,深入到背后,我们会发现那都绝非偶然:现有的资源和制度往往决定了群体选择,而这种选择本身又决定了未来走向。从这一意义上说,充满争议的时刻正是因为它还存在着不同的道路,我们以为只是在为自己做出选择,但实际上,我们很可能也在为后人做出选择。

《恐慌帝国:传染病与统治焦虑》
[英]白锦文 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年12月版
文章作者

美国新生儿不用接种乙肝疫苗了?专家:疫苗仍是中国肝炎防控重要手段!
目前全球结核病低发的国家中已经有一部分不接种结核病疫苗了,美国提出取消肝炎疫苗的接种是基于美国的慢性乙肝处于很低的流行水平。但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

聚焦防治三大传染病,全球基金在南非G20峰会前筹资113亿美元
目前因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死亡的人数较二十年前已至少减少一半。

豪华邮轮成诺如病毒重灾区!感染后应采取哪些措施?
除了通过被污染的食物进行传播之外,诺如病毒也会发生直接的人际之间的传播。“一旦在船上发生疫情,很难控制住。”

张文宏团队开发出新型检测试剂,结核病筛查试剂成本降至不到1美金意味着什么?
结核病是全球当前面临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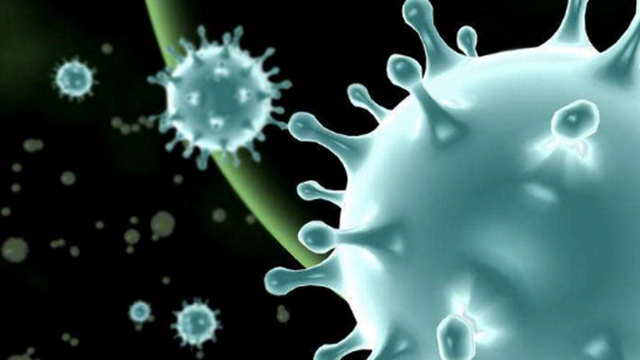
一校2087人感染!国家卫健委:诺如病毒在地下水中数月仍具感染性
诺如病毒冬春季高发,婴幼儿、老年人更易发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