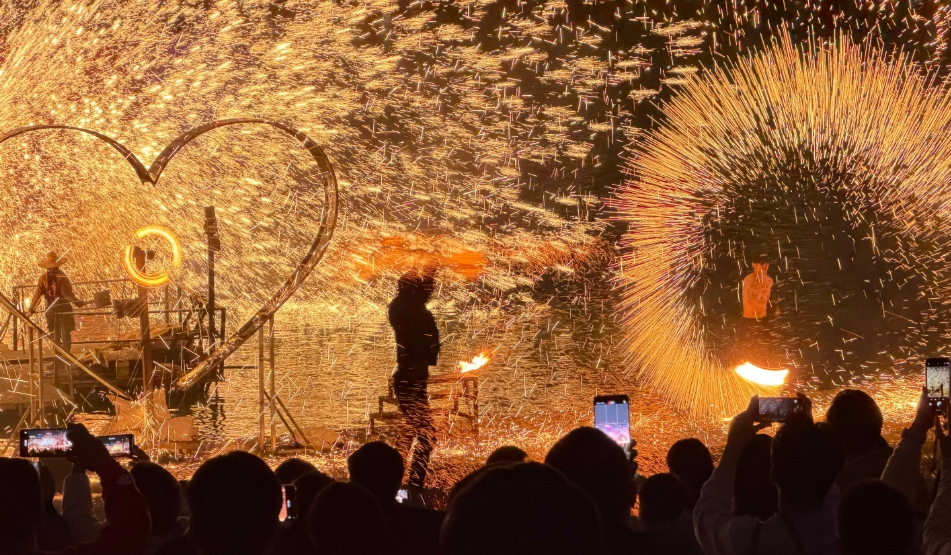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尽管腿上打了石膏,走路需要拄拐,69岁的阿拉坦其其格依然带着她的“草原之声·内蒙古长调演唱团”,于2月初登上北京中山音乐堂舞台。
临出发前20多天,这位第一批国家级蒙古族长调民歌代表性传承人在一场演出中不慎滑倒,但腿伤没能阻挠她的行程。在北京彩排现场,哪怕难以移动,她也靠着口头指挥,像将军一样统筹每个细节,毫无疲态。
“骂人骂了一天。我嘴上肯定凶,不是一般的凶。”拄着拐杖缓步走到后台休息室时,阿拉坦其其格笑起来,人也松懈下来。她的精神依然饱满,中气十足,一边张罗演出前的细节,一边化妆准备登台。

“蒙古长调无所谓舞台,走到哪里都能唱。但对这些孩子来说,今年他们能有福气站上首都的舞台,很重要。”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她感叹,16年了,终于把自己教出来的32个孩子从草原带到北京。这场演出不一定很专业,但对她和这些孩子而言意义非凡。
2008年,阿拉坦其其格在家乡阿拉善右旗的沙漠深处成立“阿拉坦其其格蒙古长调传承培训中心”,面向牧民的孩子做免费公益培训。16年里,她教过的孩子超过1100个,有人甚至从美国慕名而来,其中有20多个最终以蒙古长调为专业,考大学、读研。在青海、内蒙古等地,她也建起8个长调基地。
“我从小就唱长调,我这一生的挚爱和职业也是长调。”常有人问阿拉坦其其格,蒙古长调会不会失传,被其他音乐淹没、遮盖?“我说,如果我们都去做传承,长调不会失传,就看你怎么做。”说到这个话题,她爽朗地笑起来。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杨玉成与阿拉坦其其格有30多年交情,在他看来,作为一位蒙古长调大师,她能放下歌唱家的光芒,面对一群孩子,凭一己之力坚持做那么多年的公益普及,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都难以想象其中的苦,但在她的字典里,就没有苦这个字,她一直都在说,做这件事很幸福。”
“她不是封闭起来做传承,而是为牧民的孩子敞开一扇开阔的大门,让他们在蒙古长调的源头上去回溯家乡的民族音乐,了解牧民生活,融入自然,知晓蒙古族文化,再把长调引入到现实世界。”杨玉成说,这种民族音乐的普及方式,既艰辛也可贵。
16年,8个基地,1100多个学生
北京的这场蒙古长调音乐会,像是一场等待了十几年的聚会。
后台站满了穿着五颜六色蒙古族服装的学生,她们7岁到23岁不等,身高参差不齐。其中有刚加入集体的,也有像敖斯尔卓玛这样,从7岁就开始跟着阿拉坦其其格学习,现在已经23岁的成年人。敖斯尔卓玛以蒙古长调为专业,不仅参与演出,业余时间也帮着老师义务上课,是新一代之间的传承。

2008年3月,阿拉坦其其格将自家的牧场辟出来做教学,那里远离城市,空阔辽远,有着唱长调最需要的自然环境,“周边除了草场,就是骆驼、羊群、沙漠和戈壁”。
第一批孩子来了30多位,从小学生到高中生都有。孩子们来住上一个月假期,只用缴纳三四百元的基础伙食费,吃住都在一起。阿拉坦其其格既是老师,也承担着养育者的角色。大一些的学生跟着她一起下厨做饭,年幼的就在大自然里撒欢玩耍,与周围的牛羊和骆驼为伴。
她教孩子们长调,也教她们传统的蒙古族文化和礼仪,“蒙古长调不是哪个作曲家的创作,而是靠祖祖辈辈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孕育出来的音乐。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大草原的场景里创作,今天的孩子也要在这样的自然中学习长调,才能懂得蒙古族灵魂的音乐内核。”
杨玉成最早听说她要回归草原,针对孩子做蒙古长调的公益教育,并没有当一回事,“我以为,她就是趁回内蒙古的时候,在家乡召集一些孩子玩一玩,没想到一做就是十几年”。
十几年里,杨玉成也安排了自己的研究生到基地里协助教学,看到学生们发来的视频,他才发现,阿拉坦其其格是真的把这件事当作事业在做。
“牧民一到假期就把自己的孩子送过去,大家不但学唱长调,还一起生活,她带着孩子们放牧、做饭,学习蒙古族的民间传统礼仪和文化,完全浸泡在蒙古族的生活里。”杨玉成说,这种坚持了十几年的持续付出,让他刮目相看。
他常问阿拉坦其其格,有没有什么困难,她却从没埋怨缺少支援,也不把这件事叙述成一件崇高的事业,只是年复一年埋头去做,“她从没有开口向政府要钱,就是凭自己的心去做,在其中获得快乐”。
说到这16年,阿拉坦其其格语速轻快,“这件事,有钱我要做,没钱一样也得干。不行就去搞一些活动,但很多时候,真的是没钱,心就塌掉了,打击特别大。好在这十几年,总是有贵人在帮忙。”
她得到过一些基金会的资助,但基地上每年接待如此多孩子,吃喝拉撒、缝缝补补都需要钱。这次北京演出,她需要两万元资金,也是向各位家长集资借款。
阿拉坦其其格对待教育很严格,面对几十个孩子时,她总是恩威并施。在北京演出的重要时刻,她也很难松懈哪怕一刻。
“我们到北京演出,就是想让更多人了解蒙古长调。”阿拉坦其其格说,这场演出的每个细节都由学生和学生家长参与完成。有人负责节目册设计印刷,有人负责筹款,有人负责团队出行,有人在后台张罗事务。
演出当天,一些学生赶来现场,鲜花摆满了休息室。她的第一位硕士研究生王连福说,阿拉坦其其格不仅是歌唱家,也是教育家,在中央民族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等学院做客座教授。阿拉坦其其格培养了许多顶尖的蒙古长调歌唱家,其中包括在《乐队的夏天》中以蒙古长调引发关注的安达乐队主唱。
“老师在上课时像个将军,私底下又像个少女。”王连福还记得,老师对艺术要求之严格,常让学生绷紧神经,“我以前总是边唱边哭,知道没达到老师的要求,很惭愧。”
“这些年,我在基地教了一千多个学生,目的并不是培养长调的专业歌手,而是要让足够多的孩子知道长调,让长调在这片土地上继续生长。”阿拉坦其其格说,只要多一个孩子接触过蒙古长调,就像播下一粒种子,长调的根基就不会断裂。
《金色圣山》,一个家族三代女性的命运
杨玉成去过阿拉坦其其格家里,对她家印象极为深刻。
一进屋,贴着两张对联,上面是两首蒙古长调的歌词,一首《金色圣山》供奉给姥姥,一首《后背上的马驹》供奉给姥爷。
哀伤凝重的《金色圣山》,是阿拉坦其其格著名的蒙古长调歌曲,也是串联起阿拉坦其其格家族三代女性的一首歌。
1944年,阿拉坦其其格的姥姥去边疆看望生病的妹妹,结果刚离开几天,国境线划分,往返两地的路被中断,自此无法返回。年幼的三个孩子跟着姥爷长大,想不到一别就是接近半个世纪。
阿拉坦其其格小时候常跟姥爷放牧,发现他总是盯着远方的山脉出神,有时就唱起《后背上的马驹》,有一句歌词大意是,“我亲爱的人,你在哪儿”。每唱到这句,姥爷就默默落泪,被不知情的孙女笑话。
“现在想起来,妈妈当时唱《金色圣山》,也是在思念自己母亲。”阿拉坦其其格说,姥姥漠古年轻时是金嗓子,常被邀请到婚礼上唱《金色圣山》。姥姥将这首歌教给母亲达西玛,达西玛又将这首歌教给了她。
她回忆小时候生活的牧区,就在阿拉善沙漠边上,“从小就听妈妈唱长调,我跟她一边放牧一边唱。骆驼、草垛、高山、白云都是我的观众。有时候就把石头堆起来,把它们当成观众,给它们唱歌、跳舞、说话。”
“长调一唱起来,就像直接在跟宇宙对话。一唱起长调,眼睛里都有画面。”阿拉坦其其格说,蒙古族不仅是“有宴必有歌”,在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中,长调既是心灵的咏叹,也是日常的娱乐。
她记得,家家户户到了过节的时候,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幼年时的她最盼着过节,可以吃到馍馍和糖块,可以跟大人坐在星空下,在篝火边唱歌。常常是孩子们都困得睡过去了,聚会还未散场,“有时候睡着了,做着梦,还在唱,梦见自己骑着骆驼放声唱”。
阿拉坦其其格出生成长的阿拉善,是世界第三的大沙漠,地广人稀。如果要去一个邻居家拜访,必须早早出发,很晚才能到。“阿拉善的长调比较悲凉、宏厚。有时风刮起来,天地都掩起来了。在这个环境里,人就像骆驼一样,有一个往前走的精神。这个地理环境把当地人的心理状态、行动和音乐塑造得与其他的地区不一样。”
蒙古长调咏叹生命、自然万物,也唱亲情与思念。蒙古族无论悲伤还是喜悦,都会以歌声传情,把那些无法言说的情感寄托在歌词里,飘散在草原的野风中。
《金色圣山》更像是阿拉坦其其格一家三代女性的精神连接。1993年,阿拉坦其其格在乌兰巴托举行的第一届国际蒙古长调比赛中以这首歌夺得金奖。获奖后,她的歌声出现在蒙古国的收音机里,80多岁高龄的姥姥漠古听到这首歌,就像打开时光隧道,认定唱这首歌的人一定是自己家族的孩子。姥姥最终找到阿拉坦其其格,跟三个已经垂垂老矣的孩子团聚,度过她生命的最后时光。
1995年,阿拉坦其其格的家族故事被拍摄为一部蒙古长调纪录片《金色圣山》。
无论是看这部纪录片,还是在现实中与阿拉坦其其格母女交流,杨玉成都有一种奇妙的感受,尽管这对母女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但两个女性就像是跨越了时空与时间,凝聚为一体。就像草原上的男人与骏马,阿拉坦其其格与母亲的情谊跨越了亲情,是现代人难以理解的,“她们之间不仅血脉相连,更有相同的信仰和共同的价值观”。
杨玉成在两位蒙古族女性身上,看到的是超越平凡的坚韧。母亲从小失去母爱,11岁就放牧养家,走南闯北。阿拉坦其其格从草原上开始唱歌,一直把歌声唱到国际舞台,荣获大奖。在丈夫去世后那几年,阿拉坦其其格一度消沉,但又很快振作起来,跟母亲一起做公益培训基地,把积攒多年的能量奉献给普通牧民的孩子。
阿拉坦其其格说,蒙古长调民歌已经走过千百年,都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才流传至今。在一代又一代蒙古家族中,长调出现在夜晚的篝火边,在马背上,在草原辽阔的风中,在婴儿熟睡的床边,所谓传承就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杨玉成认为,阿拉坦其其格是蒙古长调的集大成者,她将传统唱法与现代歌唱技巧融会贯通,她把不同区域的长调风格融合在一起。早年,曾有长调歌唱家尝试这么做,都无疾而终,她却寻找到自己的唱法,并且演变为一套成熟的长调教学体系。
十多年前,阿拉坦其其格发现长调面临断层危机。老一辈长调艺术家相继去世,城市化的进程越来越快,年轻人离开草原,离开家乡,长调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她与母亲去做蒙古长调传承培训中心,全是出于对蒙古长调的热爱,以及越来越强的紧迫感。
“长调是蒙古族的灵魂,流淌在蒙古人的血液里,刻在蒙古族人的骨头上,是特属于这个民族的唱法,唱出来的就是我们蒙古族的自然环境和生活方式。”她常说,自己是草原的孩子,为蒙古长调做一点事情,她获得更多的是幸福和知足。
“她始终扎根于戈壁沙漠,从一个草根蜕变为顶级歌唱家,在蒙古长调的歌唱家中,是前无古人的。”说起这位年龄相差20岁的忘年交,杨玉成说,在阿拉坦其其格身上,他看到了女性最坚韧的性情,“她将近70岁的人生,活出了普通人的三辈子”。
前几年,母亲去世,对阿拉坦其其格的打击极大。她在传承长调时,像是在完成自己家族持续了三代人的梦想,但母亲离开,她失去了左膀右臂,没了支持。
说起母亲去世,她会突然眼神黯然。随着年龄渐长,谁来接管基地,也是疑问。
但每次她去到基地,跟孩子们生活在一起,投入时间上课教学,看到来自美国的孩子也出现在课堂上,踏实做事就变成了眼下最让她快乐的事情,“只要蒙古族存在,蒙古文化存在,长调就不会失传,这是我们一代又一代蒙古族的任务”。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