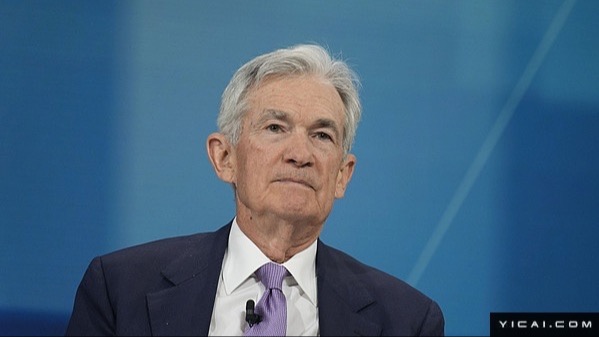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本文作者张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需求不足是一种并不罕见的市场失灵现象,处理不当破坏力很大,经济社会运行方方面面都受影响。国内外历史上有很多需求不足的案例,上世纪20年代末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不足,当时大部分工业化国家经济崩溃。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主要原因是需求不足,日本经济一下子从神坛跌入谷底。对于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需求不足更频繁地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民生的挑战。
我国近十年来频繁遇到需求不足挑战,需求不足环境下,哪怕产业升级和经济资源配置效率还不错,供给还不错,但是由于需求跟不上,经济增长就缺少获得感。收入和盈利增长压力持续时间长了,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也会减弱。
理解需求不足的本质
我国近年来采取了很多措施应对需求不足,但迄今为止尚未走出需求不足局面,需求不足的危害有进一步放大的迹象。通过加深对需求不足的理解,透过错综复杂的现象认清需求不足的本质,才能在决策上面挡得住噪音,下得了决心,真正阻断需求不足。完整地理解需求不足,需要很复杂的宏观经济模型才能做到,这里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需求不足的要害在什么地方。
屋子里面有A、B、C三个人,每个人都花钱向另外两个人购买商品和服务。每个人花掉的钱,会成为其他人的收入。因为某种原因,屋子里面的A突然不愿意花钱了,结果会怎么样?A的支出下降会带来B和C的收入下降,B和C的收入下降会带来B和C的支出下降,B和C的支出下降又会带来A、B、C 的收入下降,这样就形成了收入和支出下降的负向循环。
在上面这个例子基础上更进一步地说。屋子里面除了有A、B、C三个人,还有一个名字叫做D的银行,三个人都有银行的存款和贷款,三个加在一起的银行存款数量等于贷款数量。出发点还是A突然不愿意花钱了,结果会怎么样?与上面例子相同的是,这会带来收入和支出的负向循环。不同的是,在 A、B、C三个人的负向循环中,对未来的盈利预期和收入预期都会下降,不敢举债投资,更倾向于偿还贷款,全社会的信贷规模下降。由于贷款的下降,A、B、C 加在一起的银行存款数量也会显著下降。越是不贷款、越是还钱,A、B、C加在一起的钱越少。对于加入了银行和信贷的例子里面,全社会钱的数量(信贷)也会显著下降,而钱的数量(信贷)下降会让负向循环进一步加剧。
从历史经验来看,需求不足的负向循环过程中,最大的加速器是信贷下降。信贷下降让全社会的钱包变小,带来支出和收入下降,这又会带来更大幅度的信贷下降,如此自我强化,需求不足越来越严重。相比支出和收入的变化,信贷的变化幅度更大,信贷下降成为需求不足负向循环中的最大推手。
从中国近些年的情况来看,名义GDP增长速度代表了支出的增长速度。名义GDP增长速度可以分解为广义的信贷增长速度(主要是贷款和债券)与名义GDP/广义信贷增长速度之和,前者可以理解为全社会钱包的增长速度(取决于贷款和发债),后者是给定钱包下的支出变化。
对比2012-2019年和2021-2023年两个时期,名义GDP增长速度从9.0%降到4.7%。广义信贷在后一个时期比前一个时期的增速下降了5.8个百分点,大于名义GDP增速的下降幅度。这告诉我们,过去几年需求不足主要来自信贷下降,来自全社会钱包的增长速度大幅放缓,而不是给定钱包下的支出下降。
通过这个例子还应该看到,需求不足是一个新的、独立的现象,脱离了造成需求不足的最初诱因。对于需求不足,最受关注的解释是收入分配恶化:穷人没钱消费,钱都去了富人那里,而富人又花不了那么多钱,所以需求不足。然而仅从历史数据来看,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拉大的时期需求不足并不严重,反而是近十年来收入分配差距相对平稳时期需求不足更加突出。
从机制上面看,即便是收入分配恶化,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造成了最初某一方的支出下降,形成了需求不足最初的诱因,但是一旦形成收入、支出和信贷的负向循环以后,问题的性质就变了,需求不足就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问题。需求不足的本质在于收入、支出和信贷的负向循环,而不再是收入分配恶化或者其他的什么诱因。
这有点像SARS和新冠病毒是最初对人身体健康伤害的诱因,但是真正让伤害放大甚至致命的不是病毒,而是人身体的过度免疫风暴。收入、支出和信贷的下滑,都可以看作是微观个体对自身保护的理性做法,但是这些保护做法加在一起的时候,对整体造成了更致命的伤害。
阻断需求不足需要抓住关键
一是阻断需求不足,关键是管住快变量。支出当中,消费短期内很难有大变化,投资短期内可以有很大变化,消费是慢变量,投资是快变量。收入当中,劳动者收入短期内很难有大变化,企业盈利可以有很大变化,劳动者收入是慢变量,企业盈利是快变量。信贷本身短期内可以有很大变化,是快变量。在需求不足的负向循环当中,造成负向循环加速度的是“投资—企业盈利—信贷”之间的负向循环。阻断需求不足,关键在于阻断这个负向循环。
很多学者建议,中国应该增加消费,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劳动者收入,这些建议从长期改善经济结构的角度看非常正确。但是,需求不足是个独立于结构失衡问题的问题,历史经验中很少有在短期内主要通过大幅提高消费和劳动者收入阻断需求不足的案例。阻断需求不足中的负向循环,关键还是管理好短期内可以有很大的变化的快变量,管理好投资、企业盈利和信贷,尤其是信贷。
二是阻断需求不足,关键是用对逆周期政策。凭借市场自发的调节机制,并不能让需求不足自我修复。降低利率和政府举债扩大支出,是经过国内外反复实践,可以在短期内阻断需求不足的成熟、有效的做法。这些做法可以在短期内给居民、企业和政府资产负债表带来巨大变化,有针对性地打破投资—企业盈利—信贷之间的负向循环。
一种普遍的担心是逆周期政策会不会破坏市场,会不会带来太多后遗症。需求不足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是市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的表现。需求不足时期,充分使用降低利率和政府举债扩大支出这些逆周期政策,是修正市场失灵,让市场恢复正常功能,这是对市场的保护,也是对未来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保护。
三是逆周期政策力度小了不行,小了就成了添油战术。阻断需求不足必须是足以打破负向循环加速下沉力量的强大外力。日本“失去的二十年”是个很典型的负面案例,1992-2012年期间日本面临持续的需求不足,日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能说无动于衷,但总是犹犹豫豫不坚决,逆周期政策表态和力度不坚决,经济稍有恢复又急于退出宽松政策,结果是经济稍微好一点就再次下行。直到2013年安倍政府上台以后,日本情况才有了转折性变化,最突出的是宽松货币政策表态非常坚决,随之而来的是日经股票指数翻倍,失业率下降超过2个百分点,通胀率明显回升,日本经济走出了“失去的二十年”。
真正能发挥功能的逆周期政策,必须是非常坚定地表态和超预期的政策力度,表态越坚决,越超预期,改变市场预期的代价越小,政策空间消耗反而越少。
四是当需求不足成为最突出挑战的时候,全力阻断需求不足应该成为最优先事项。维持经济健康运行有各种各样的障碍,比如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营商环境不够好、贪污腐败、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合理等等,相比之下,严重的需求不足对经济的伤害最致命。好在只要逆周期政策力度够了,需求不足问题可以很快得到解决。
就当前而言,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存量、对金融和其他行业的治理和整顿、优化政策支出结构等都是长期工程,需要破旧立新。但是破旧立新是会带来经济短期内的脆弱性,如果再叠加需求不足给经济带来的脆弱性,会形成脆弱性的叠加,给短期经济带来过大压力。
当需求不足来袭,集中精力阻断需求不足,问题就可以很快得到解决;对待破旧立新类型的问题,可以“风物长宜放眼量”。先把需求不足这个最大的威胁解决好,很多需求不足的次生灾害少了,解决其他更长期的、结构性的问题会有更大腾挪空间,破旧立新也更容易成功。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