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萨特—加缪之争”今天还有热度吗?两位男性公共知识分子,两位卓越的法国文学家,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场说不尽的恩怨。事情发生在遥远的70多年前,但是人物依然新鲜,特别是加缪,《局外人》《鼠疫》的影响力历久弥新,文字里处处散发的人格和思想依然使人着迷。小说之外,加缪还发表戏剧、散文和思想论著,其中,1951年出版的论著《我反抗,故我们存在》(原书名《反抗者》)最近有了一个新的中译本,它写于二人关系由热转冷之时,更写于冷战开启前后,一个社会高度分裂的时代。
从加缪的笔记里,能看到《我反抗》的写作时间是1946年,《鼠疫》在那年出版,但那是个战争刚刚结束的冬季,因物资短缺、人心忧伤而显得格外寒冷。那时,加缪在一个阿尔卑斯山中的旅馆住着。他才33岁,已是名作家,也是声誉达到顶峰的政治左派,可是写此书时,心情并不好。
“一个人度过了一周,我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我的能力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一开始时我很狂热,现在想要放弃。”
这项工作就是写作《我反抗》。战争结束,似乎能松弛一些了,然而加缪眼里已经有了一幅现代图景:在自由的旗帜下,以正义,以慈爱,以未来,以超人崇拜……以各种名义继续大肆杀戮。从法国国内的“肃奸”,即肃清在之前4年与德国占领者合作的法国人,导致矫枉过正开始,每个人就都活在一种有毒的政治空气里,简而言之,每个人都被要求自证清白。为此,暴力的滥用打开了大门,不能自证者,或是不想自证者,都在暴力的威胁之下。

这是什么情况?加缪在一片含混之中敏锐地看到要点:不管以什么名义,恶的或是善的,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结果都是暴力被正当化。因此要紧的不是论证对错善恶,而是停止正在发生的暴力本身。这不需要太多的理论撑腰,而只需要一种朴素的道德感。
在《我反抗》写不下去的时候,加缪就读蒙田随笔。蒙田是16世纪人,可是他的思想从幽深的地下直接射入现实。在蒙田的时代,法国和加缪的时代一样陷入分裂,不同的宗教教派各举大旗,讨伐敌方,称其为异端。蒙田有一篇《为雷蒙·塞邦辩护》,很长,经常被拿出来做成单行本。蒙田说,“神圣学说”被无耻地玩弄在各种势力手中,人们按自己的需要使用它,解读它,或是抛弃它。蒙田深沉地写道:人不能超越自己和超越人性,人只能用自己的眼睛观看,用自己的手来抓取。
我的眼睛看到了暴力,我就要反对它,而不用管这个暴力是打着怎样的名义——这就是蒙田设下的简单的标准。加缪认同蒙田的伦理学。他在不同的文学创作里,都写入了这样的道德纯粹的人,例如《鼠疫》中的塔鲁,他在法庭上目睹检察官父亲慷慨斥责一个被告人,非但没有觉得父亲代表公权力的威严,反而厌恶不已,因为他眼里没有“代表”,没有抽象的“正义”,而只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凌驾,以及声音洪亮的暴力诉求。在1949年问世并公演的剧本《正义者》中,加缪更是塑造了年轻的恐怖分子卡利亚耶夫这个角色,他在受命刺杀莫斯科大公的情况下,因为看到大公身边有孩子,而一念之间没有下手。
卡利亚耶夫因为自己的心软遭到同党的唾弃和惩罚。这是加缪心目中理想的“反抗者”,他要反抗自己眼里的不公平,可是“公平”与否是个抽象观念,反抗行为最终总要对个体下手,此时,反抗者的行为抉择就必须诉诸朴素的良知。当他发现自己难以动手时,他落入荒谬处境,目的和行动之间达不成一致,想要实施正义的人得先染污自己的两手。这种处境导致反抗者的极度厌恶,他继续反抗,反抗这个无法推翻的处境,承受随之而来的巨大的孤独感。
虽然在写书时遇到困难,但是加缪在战后的政治知名度一直在上升,他主张反对所有政治暴力。20世纪5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开始发生骚乱,作为一个老牌殖民帝国,法国终于也要面对第三世界殖民地独立浪潮的冲击。阿尔及利亚出现了惯于搞恐怖活动的民族解放阵线,法国军队在当地也实施抓捕,施加臭名昭著的酷刑,对此,加缪写文章,同时控诉两者危害平民的暴力。他完全实践自己的理念,不管萨特怎么看他,怎么嘲讽他幼稚、天真的道德主义。
1951年《我反抗》终于写完出版。加缪究竟写了些什么,他是怎么把自己的反暴力理念“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呢?
任何哲学思考,都要有一个起点。“反抗”就是加缪的起点。这个起点不可再简化。笛卡尔的起点是“我思”,先确认一个思想着的“我”是实在的,所谓“我思故我在”;相应的,加缪的箴言是“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为什么反抗是存在的起点呢?加缪说,因为人总归要意识到荒谬,也就是说,人总归要意识到自己会死,意识到这个世界对我的生死苦乐无动于衷,意识到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偶然的,并在成人之后,拥有一个日渐支离破碎的自我。所以,人要通过反抗,来克服荒谬。
于是他做了一份自己的“读史札记”,从反抗的角度来重看一些节点性的事件、人物和思潮:希腊人,早期基督教,法国革命与萨德侯爵,浪漫主义,《卡拉马佐夫兄弟》。各种各样的思潮,从黑格尔、马克思到尼采,从超现实主义、纳粹到布尔什维克。加缪说反抗的力量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长,进入一种更加绝望的虚无主义,颠覆上帝、取代人类,越来越残忍地行使权力。这就是“历史(中)的反抗”,它根源于形而上学的反抗,却导致了革命——革命企图用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绝对权力来消灭荒谬。
那么怎样反抗才是正当的呢?那就是更懂界限、更温和、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反抗——“学着自己活,也让别人活,以创造我们的本质”。加缪试图澄清反抗的基本精神,摈除它被严重歪曲的版本,追溯其更加谦和、适度的起源。结合《正义者》来看,加缪理想中的反抗可谓一种秉持贵族操行的行为,“贵族特质就是不问为什么就去奉行美德”。
在《反抗者》即将出版前,加缪和萨特的关系有很大的缓和。因为萨特的戏剧《魔鬼与上帝》正在排演,而女主角玛丽亚·卡萨雷斯正是加缪的相好。萨特在他的《现代》杂志上刊发了《反抗者》中谈尼采的那一章。那确实是雄辩的一章,加缪把尼采的反抗如何被推崇他的人(比如希特勒)转换为“对恶的歌颂”,细细地说了出来:
“在尼采的思想中,恶只是人面对无法逃避的事物时,傲然接受的一个东西。然而,我们很清楚,他的思想继承者,以尼采的思想为基础发展出什么样的政治。他曾创造出暴君艺术家的形象,但对平庸的人而言,残暴比艺术来得容易……”
尼采思想被政治暴徒狭隘地利用,“人们借用他的名,反过来让愚勇扼杀智慧,让他真正的思想逆转成全然相反的:触目惊心的暴力”。虽然这一章被萨特所接受,然而整本《我反抗》的要旨是和萨特的政见相反的,正如《正义者》和《魔鬼与上帝》也是唱反调的。《正义者》呼唤贵族式的反暴力美德,卡利亚耶夫从一个革命恐怖分子转变为加缪理想中的反抗者,而在《魔鬼与上帝》里,主人公格茨从一个信仰反抗的人,一步步“找到组织”,投身于具体的、暴力的革命。
主动接受暴力,弄脏两手,就意味着拥抱现实,成为一个不抱幻想的现实的人。在《我反抗》里,加缪明确地把自己同“存在主义者”的阵营划出了界线,同时向萨特们下了战书。
这两位思想领袖的对立,使得1945~1952年间,想要找到方向的法国知识分子都别无选择,必须表态支持其中的一方。这种情况本身也很荒诞,因为加缪本人最讨厌站队,他一直所持的就是一个中间立场,温和的,理性的,渗透了贵族道德的。然而他却被“对标”了,其他人必须要么拥护他,要么反对他,正如他也必须站在一个反萨特的位置上,来树立自己的道德立场。
此种特殊的情况,也反映在了《我反抗》的语言风格里。加缪的文风,一直是以简约、动情、精确入微著称,从《局外人》到《鼠疫》,再到他晚期未能完成的自传体小说《第一个人》,他的成熟肉眼可见,他的风格中最有趣的特点之一,是一面刻画贫穷、疾病,刻画孤独和单调乏味的生活,一面给人注入一种自然而然的昂扬的热情,凭此,他也向存在主义的根本命题——生在荒谬世界上的人如何自由地活下去?——给出了一种婉转的回答。
可是《我反抗》却不同。这本书里,下判断的地方非常多,前一句和后一句之间,逻辑关系有时不很清楚。每个句子都是细心推敲过的,都能反映加缪的核心思想,不过,句子和句子之间缺少连接,在本该展开论述的地方,加缪会停下,续上另一个细心推敲过的句子。
这不是一本“娓娓道来”的书,而是一本论战之书。后来的学者们、传记作家们,为如何评价这本书而展开争论,有的人从文字—思想质量本身出发,把它贬为加缪的失败之作,有的则强调了创作此书需要的勇气,认为应该把它看作一种可敬的政治行为,而不是一部“作品”。从加缪的笔记,我们可以看到,他一直就以写了《我反抗》而自豪,他知道自己承担了多么大的名誉风险:他将不再是一个受到左翼力量推崇的文学英雄,同时,右翼分子因为《我反抗》里对革命暴力的谴责而赞美此书,却也不会按照加缪本身的成就来承认他的价值。
勇敢固然是勇敢,但加缪所持的那种不可救药的浪漫的、诉诸贵族传统的立场,一定无法在那个年代获得足够的拥趸。在政治狂热、立场先行的年代,恪守个体道德良知的加缪,势必会被孤立。萨特嘱咐他的一位追随者,在《现代》上发表长文,反击《反抗者》,随后则是那封著名的绝交信。这些不再赘言。加缪在未来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可是在1954年到他去世的1960年间,众所周知,他逐渐沉默下去。这是别无选择的,也是伟大的沉默。虽然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是多少对世界看得越来越清楚的人,都走在加缪走过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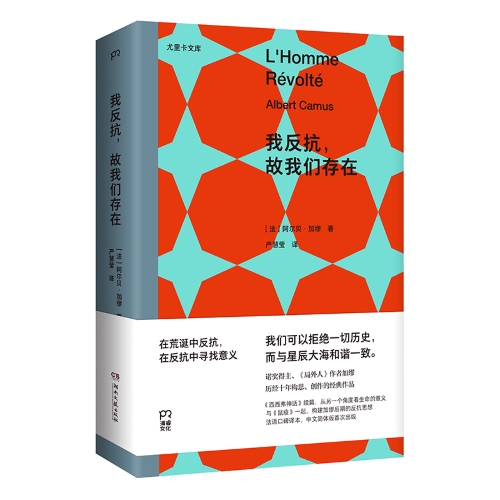
《我反抗,故我们存在》
[法] 阿尔贝·加缪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浦睿文化 2025年5月版
文章作者

市面上有五万多种膳食补充剂,哪四种确实有效?
替代医学寄托着希望和念想,也可能成为资本和骗局的温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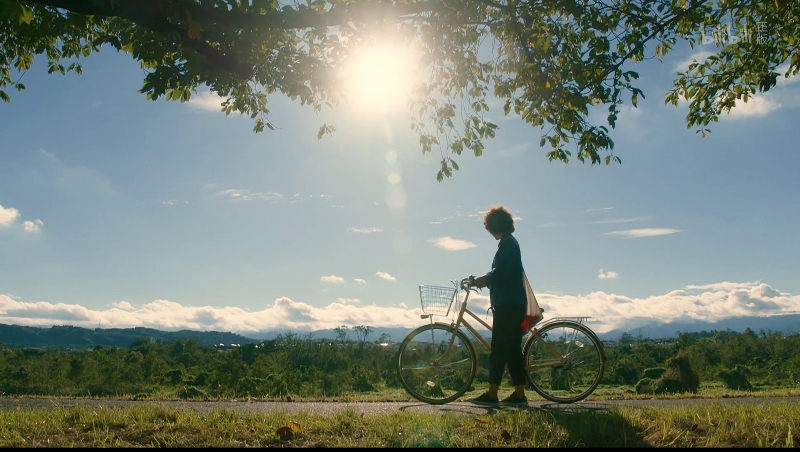
上东京还是去乡下?日本年轻人移居乡村潮流的启示
中国当代青年中也有一些人在进行扎根乡村的探索,他们可以从日本稍早的实践中借鉴什么经验?

切身可感的历史文脉,让泉州成为社媒时代的旅游热宠
“簪花与拜拜”,是当前最能代表泉州魅力的两个符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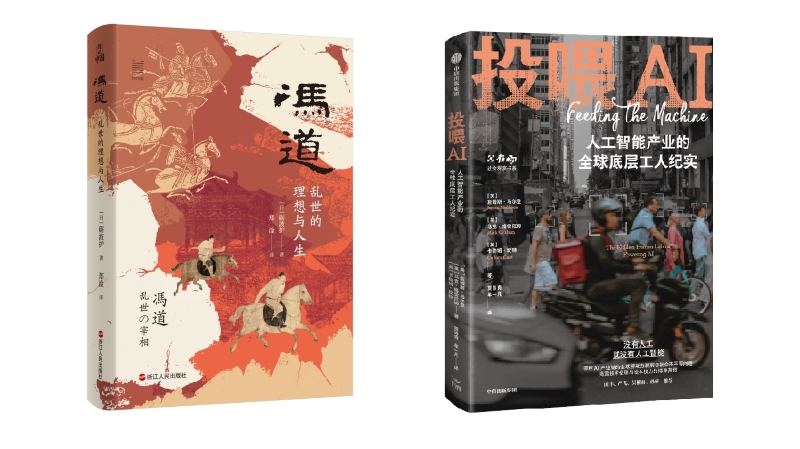
人工智能产业背后的隐形劳动者|荐书
他们或许是委内瑞拉的零工劳动者,以微薄报酬为自动驾驶汽车标注数百万张图像,却从未见过真实的汽车……

昔日花旗银行头牌交易员:金钱只是游戏,但生活不是
这本书中失败的部分比成功的部分更感人,因为金钱是虚假的,个人的痛苦与挣扎却是真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