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1990年3月,多伦多大学礼堂里座无虚席。享有盛名的遗传学家、进化生物学家R.C.列万廷(1929~2021)用一张玉米田的照片开场:
“把同样的种子撒进贫瘠与肥沃的土壤,你会看到截然不同的生长高度。请问,这是基因决定,还是土地决定?”
台下没有统一答案——这正是列万廷想要的效果。
列万廷是受加拿大广播公司之邀,主讲了5场“梅西讲座”。讲稿1992年被整理成《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一书,中文版直到2022年才面世,却像把30年前的火种直接扔进21世纪20年代的舆论干草堆:基因彩票、智商基因、犯罪遗传学、祖源测试、人类起源非洲说……话题越热,争议越尖锐。
列万廷的观点,被很多人视为极端,哪怕是他在大多数议题上坚定的盟友、著名古生物学家和科普作家斯蒂芬·古尔德,也不否认他的某些观点太过于激进,更不要说他的主要论敌们——前期是他的哈佛同事、“社会生物学”创始人爱德华·威尔逊,后期则当仁不让地是因《自私的基因》而声名远播、影响巨大的理查德·道金斯。

基因之争
列万廷攻击的对象,主要就是基因决定论,这乍看有点奇怪——作为世界知名、屡获大奖的遗传学家,率先将分子工具引入生物学的大拿,他显然非常了解基因对生物的重要性。在《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中,列万廷只轻描淡写地点了理查德•道金斯一次名,可能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在他看来只是一部不那么合格的大众科普书,相比之下,他更愿意和老同事威尔逊论战,并集中火力攻击当时引起极大关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
列万廷的核心观点,是人类基因组差异不足0.1%,却被包装成解释贫富、智商、犯罪的全部变量,在他看来,这等于是“把社会不平等偷渡进DNA”。列万廷指出,环境不是容器,“画眉鸟需要石子敲蜗牛壳,石子才成为环境;对啄木鸟,它什么也不是”。藉此,他试图证明:环境并非外生给定,而是生物体自己“挑选”与“改造”的。在生物的整个适应、进化进程中,到底基因起了多大比例的作用,环境起了多大比例的作用,基因中有多少碱基对参与了对生物性状的塑造,环境中又有多少因素在与生物体的互动中改变了生物的性状,所有这些都处在一个极其复杂多变的系统中,根本无法确定其中任何一种因素是否起作用、起多大作用、各种起作用的因素之间的比例构成怎样,等等。因此“人类基因组计划”即便完成了全部测序,在列万廷看来也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目的:通过比对患病者与“正常人”的DNA序列,来找出致病的基因根源。
虽然《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的主要“攻击对象”看上去并非道金斯,但道金斯本人当然意识到了列万廷对基因“决定性”的质疑威胁到了自己被广泛传播的观点,因而进行了回应,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基因差异还是基因决定。实际上,在《自私的基因》出版半个世纪后,道金斯仍不得不不断在媒体澄清:“从未说基因决定一切,我只说基因差异能解释表型差异。”他把列万廷的玉米田实验改写成“差异模型”:贫瘠土地缩小所有植株差距,肥沃土地放大差距——但差距仍由基因排序主导;第二,进化的方向性问题。列万廷与古尔德都强调生物进化中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反对目的论——实际上这也是达尔文本人的观点,而道金斯则举猎豹与瞪羚的“军备竞赛”为例:“今天的猎豹速度远超祖先,这是无可否认的进步。”在他看来,否定方向性等于把复杂性科学推向不可知论;第三,道德责任不能外包给科学——道金斯承认他的“自私”一词很容易被误读,所以在新版序言里他辩解道:“书名可以叫《利他的个体》,但市场不会答应。”他坚持科学结论与政治后果要分开讨论,否则就是“用社会正义绑架实验室”。
列万廷与道金斯之间的论战,对生物学界有持久的影响,著名行为基因学家凯瑟琳·哈登2021年出版了《基因彩票》一书,试图在两位“大人物”之间开辟一条“中间道路”:基因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拒绝承认基因的作用反而会导致“精英神话”的延续,但基因起作用的方式如同刮彩票,很大程度上源于运气,并且基因的影响可以被适当的社会政策减弱。
然而“中间道路”并没有受到列万廷本人的认可,去世前夕他还给《基因彩票》泼冷水:“彩票的前提是奖券已经写好号码,但发育扰动告诉我们,连号码都是盲盒。”也就是说,列万廷坚持自己的“极端”观点:基因、环境、随机性之间,根本就是“一笔糊涂账”,你不可能分清到底谁在起作用,起了多大作用,起的作用会导向哪里。
所以列万廷提出了基因、有机体、环境“三重螺旋”的概念,强调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基因在生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基因的表达受到环境因素的调控,同样的基因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表现型;有机体也并非被动地接受基因和环境的影响,它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来改变环境,同时也会对基因的表达产生反馈作用;环境也不是独立、抽象的存在,生物体可以通过自身的活动,从自然中构建自身的生存环境。自然的各个部分可以通过无数种方式构成不同的环境,我们只能通过研究特定的生物体来认识它的环境。这表明环境是相对的,是由生物体与自然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当前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发现,基因的表达可以受到DNA甲基化、组蛋白修饰等表观遗传标记的调控,而这些表观遗传标记又会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如饮食、压力、生活方式等。这意味着即使基因序列不变,环境因素也可以通过表观遗传机制对生物的性状和健康产生长期的影响,而且这些表观遗传变化还可能在世代间传递。这有力地支持了列万廷的“三重螺旋”论。
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制度
列万廷的观点常常被贴上“极端”的标签,很大程度上因为他的批判指向了生物学学科的根基,用道金斯的话来说,就是“否定任何可计算性”。道金斯特别担心“左翼知识分子”用“政治正确”扼杀科学;列万廷批判的,则是科学界往往不自觉地用“科学正确”扼杀公共政策。其实两者都需要我们警惕。
1990年的讲座散场时,有听众问列万廷:“那我们还能相信科学吗?”他回答:“当然可以,但请先学会不相信‘科学神话’。”
无论是否极端,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生物学的影响力早已超越了实验室的范畴,深入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列万廷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犹如一把锐利的解剖刀,精准地剖析了生物学与意识形态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我们理解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提供了独特而深刻的视角。
在大众观念里,科学往往被视为追求客观真理的纯粹活动,是超脱于社会、政治和文化之外的独立存在。然而,列万廷指出,科学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制度,与其他人类活动紧密相连,相互影响。
科学研究的开展离不开社会资源的支持,科研经费的投入、科研机构的设置、科研人员的培养,等等,都受到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制约。科学研究的方向也并非完全由所谓的“真理”指引,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社会需求和利益的驱动。例如,在医药领域,对常见疾病和疑难病症的研究投入巨大,这背后是市场需求和社会健康需求的推动;而一些基础研究,尽管对于科学知识的积累至关重要,但如果短期内看不到明显的应用价值,就很可能会面临资金短缺的困境。
科学的发展也受到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科学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实证主义和还原论的思维方式在科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强调通过对事物的分解和实验来揭示其本质;而在一些东方文化中,整体论的思想则更为突出,注重从整体的角度去理解事物的相互关系。这种文化差异会渗透到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影响科学家的研究思路和对研究结果的解读。
科学知识的传播和应用同样具有社会属性。科学成果并非一经产生就自动被社会接受和应用,而是需要经过社会的筛选和评判。一些科学理论可能因为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而受到抵制(达尔文进化论在提出之初,就遭到了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因为它挑战了传统的神创论)。另一些科学理论则反过来,会因为符合官方意识形态而得到鼓吹。
事实上,生物学、生命科学与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间异乎寻常的密切关系,它们之间(与其他科学门类相比)惊人的合拍与亦步亦趋,很值得我们深究。几个例子:大英帝国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与(被通俗化的)达尔文进化论;纳粹德国与种族优生学;斯大林苏联与李森科主义;里根-撒切尔“新自由主义革命”与混沌/复杂性科学(生态圈理论、仿生学等都是其中的重要课题)……最新的,或许是新冠大流行及其造成的“显学”,即以核酸生物科技为代表的当代生命科学,将会对应怎样的政治变迁?列万廷于新冠初起的2021年去世(据说是在夫人去世后绝食三日而亡),没来得及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但他对科学尤其是生物科技“独立性”的质疑,以及对于政治与意识形态对科学的利用的警惕,无疑有助于我们深入思考生物科技最新进展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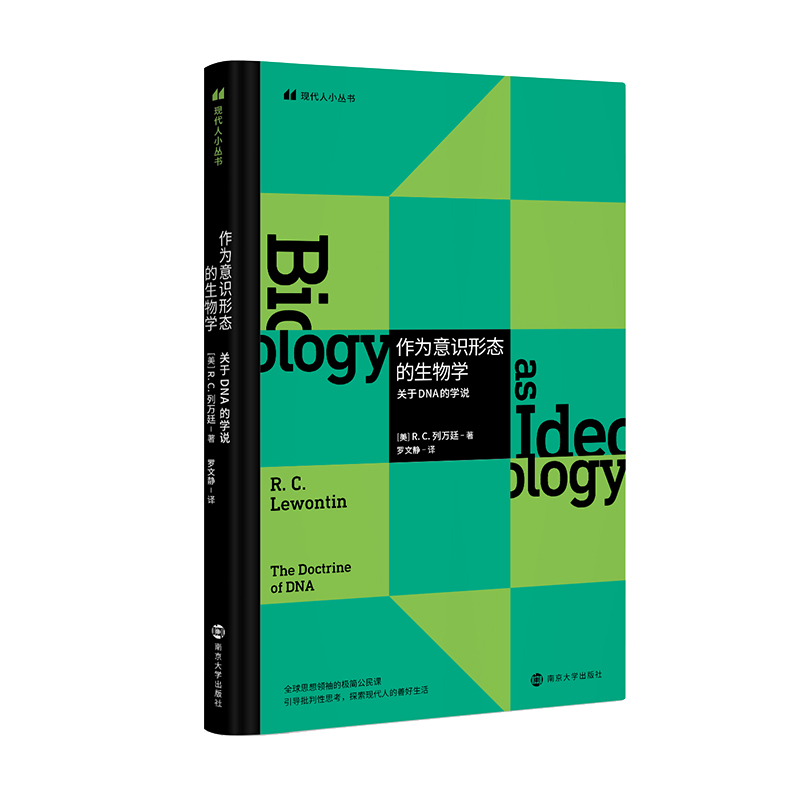
《作为意识形态的生物学:关于DNA的学说》
[美]R.C.列万廷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三辉图书 2022年8月版
文章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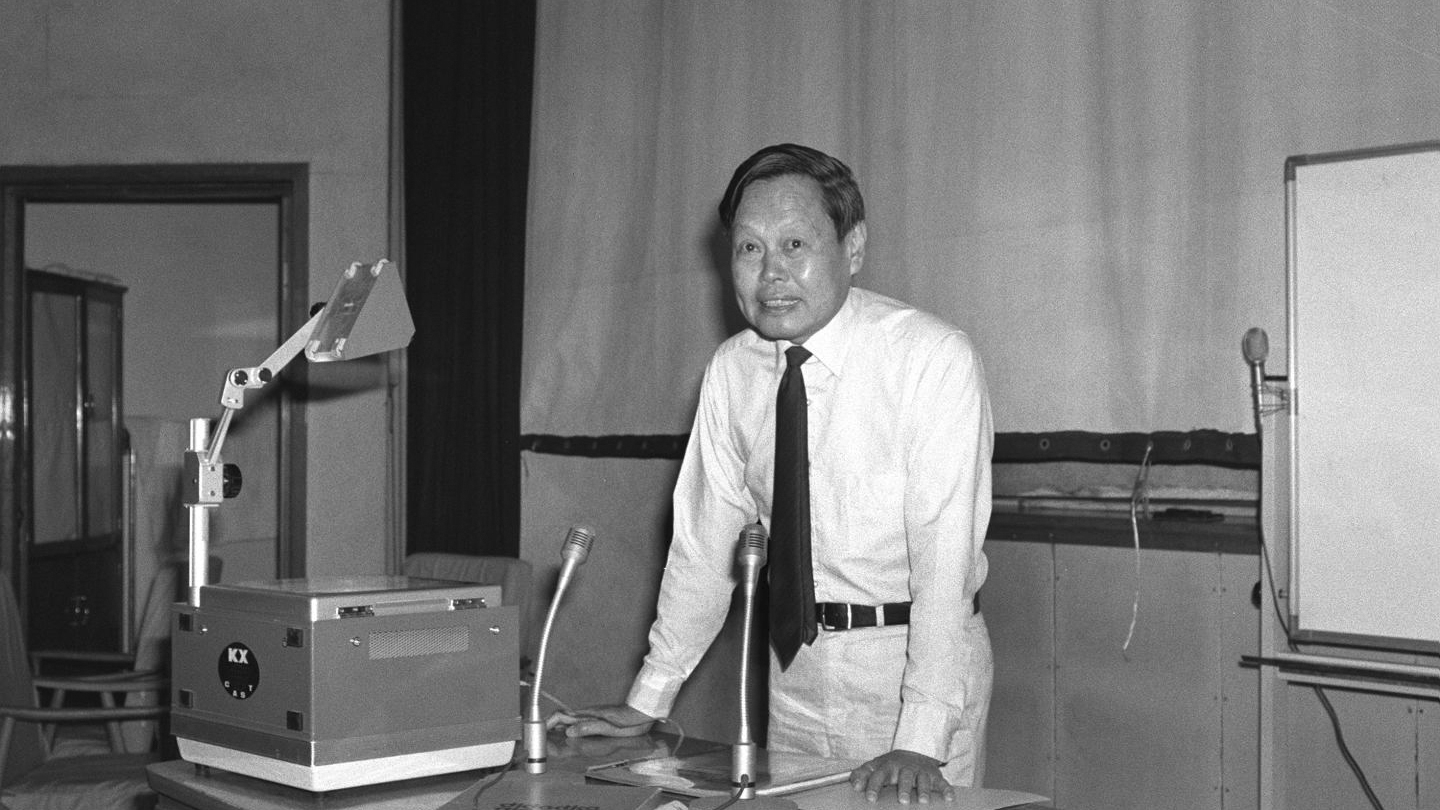
杨振宁写给中学生:把握住自己最突出的科学兴趣和天赋
杨振宁认为,那些懂得怎样动手的人恰恰是中国最需要的人才。

改变国人“自觉不如人”心理,杨振宁已在星河恒久闪耀
杨振宁在后半生将毕生所学和精力投入到引领中国基础科学研究、培养青年人才、建设一流研究机构的事业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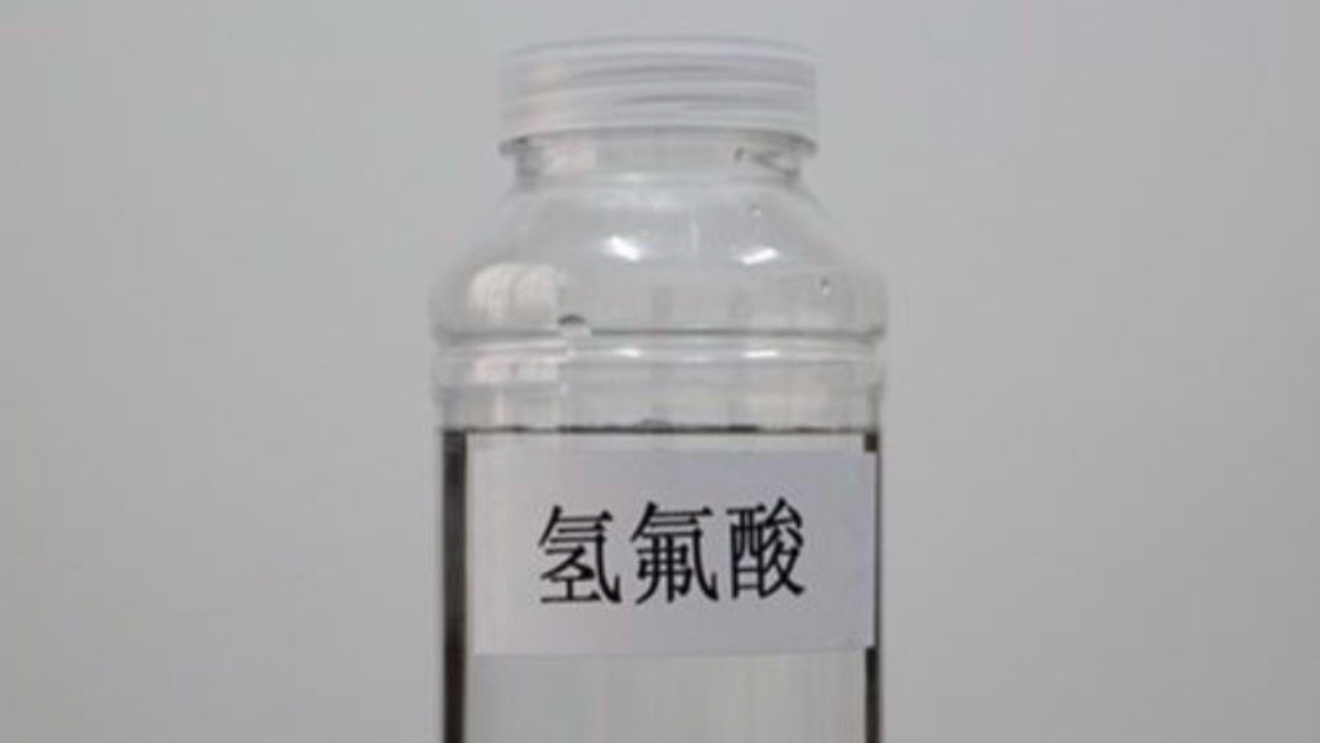
女子散步离奇中毒身亡,这种剧毒“化骨水”何以致命?
作为一种非常特殊的化学品,虽然极其危险,但在现代工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用途,是工业领域的“利器”。

“基因沉默”疗法受追捧,心脏病“疫苗”时代开启
小核酸药物具有可成药靶点多、给药频率低等优势。

从军事基地到工业区:大规模化学战对越南的影响持续至今
最新出版的《墓地中的军营:越南的军事化景观》是一本独辟蹊径的“军事环境史”著作,研究越战对越南本土环境持续至今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