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编者按】很多曾经深入了解非洲的读者——包括长期在非洲居住、工作或旅行的人——会说:“非洲就是卡普希钦斯基在《太阳的阴影》中所描绘的样子。”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是二十世纪深具影响力的作家和记者,曾经六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提名。1958年,26岁的他被派往加纳报道该国的独立庆典,并成为波兰首位常驻非洲的记者。此后三十多年间,他在这片“大到难以描述”的大陆上游荡,往返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不论是流血冲突、军事政变的现场,还是丛林中挣扎在生存线上的部落。在书中,他为读者呈现了一幅独一无二的非洲图景:那里有仿佛世界诞生之初的极致美景,也是无数部落、民族、文化和势力交织的汹涌之海。
经出版社授权,第一财经节选了书中部分篇章,以飨读者。
旅程的终点到了。无论如何,是我一直在写的这段旅程的终点。现在是在回家的路上,在树荫下稍做休息。这棵树生长在一个名叫“阿福多”的村子里,村子位于埃塞俄比亚沃勒加省的青尼罗河附近。这是一棵高大壮硕、枝繁叶茂的杧果树,四季常青。在非洲的高原上、在一望无际的萨赫勒草原上旅行的人都会看到一幅不断重复、令人震惊的画面:被太阳炙烤的沙地上,覆盖着枯黄的野草的平原上,零星散落着几个干枯的灌木丛,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棵孤独的、枝繁叶茂的大树。它那一抹绿色是那么茂盛、新鲜、郁郁葱葱,在遥远的地平线上形成一个清晰浓重的圆点。尽管周围一丝风也没有,但它的叶子轻轻摆动,闪闪发亮。在这片如月球表面般毫无生气的景色中怎么会有一棵树呢?它为什么刚好就生长在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只有一棵呢?它从哪里汲取养分?有时,我们开车要开很远一段路,才能遇到另一棵这样的树。
以前这里可能生长着许多树木,生长着一整片森林,但后来都被砍伐、烧毁了,只有这一棵杧果树保留了下来。附近的所有人都想拯救它,因为他们知道,它活着有多么重要。因为每一棵孤树周围都有一个村庄。所以,如果从远处看到这样一棵树,就可以放心地朝它走去,因为我们知道在那里会遇到人,能有点儿水喝,也许还会有点儿吃的。这些人救了这棵树,因为没有这棵树他们也无法活下去:在烈日下,人需要阴凉才能生存,而树就是这片阴凉的保管员和提供者。

如果村子里有老师,那么这棵树下就是教室。早上,全村的孩子都会跑来树下。这里不分年级,也不按年纪,谁想来都可以来。老师把一张打印在纸上的字母表贴在树干上,用树枝指着字母,孩子们盯着字母跟读。他们必须把这些字母记在脑子里,因为他们没有纸,也没有笔可以写字。
每当中午来临的时候,天空被晒得发白,所有能跑来树荫下的都躲在下面:孩子、老人,如果村里有牲畜,那些牛和羊也会来。要想熬过正午时分的炎热,在树下可比在自己的泥坯屋里待着好多了。屋子里又窄又闷,在树下地方宽敞些,还有凉风拂过的希望。
下午的时间是最重要的,村里的长者们那时会聚集在树下开会。杧果树下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他们聚在一起讨论的地方,因为村里没有更大的房间。人们非常积极,也十分乐于参加这种集会,非洲人的本性是集体主义的,他们渴望并需要参与集体生活中的一切。所有的决定都是集体做出的,纠纷和争吵需要共同解决,比如谁能得到多少耕地是要通过决议的。按照传统,任何决议都必须经过全体一致通过。如果有人有不同意见,占多数的人就会一直劝说他,直到他改变立场为止。这种情况有时会无休止地持续下去,因为这些讨论的一个特点就是没完没了。如果村里有人发生了争吵,树下的法庭不会追求真相,也不会决定哪一方占理,他们会承认双方都有道理,然后解决冲突,让双方达成和解。
当白天结束,夜幕降临,开会的人们就要暂停会议,各自散去。因为在黑暗中是不能进行讨论的,讨论的时候必须能看到说话人的脸,要看到他嘴里说的和他眼睛说的是否一致。
这时,妇女们聚集到树下,男人们和对一切都好奇的孩子们也会过来。如果他们有柴火,就会点起篝火;如果有水和薄荷,他们就会泡一杯浓浓的茶。最愉快的时光开始了,这也是我最喜欢的时光:讲述一天中发生的事情,这些故事是现实和想象的结合,有欢乐的,也有恐怖的。比如,今天早上有一个黑乎乎的、像疯了一样的动物在灌木丛中发出声音,那是什么?飞过山顶又消失了的奇怪的鸟是什么?孩子们把鼹鼠赶进了洞穴,然后他们挖开洞穴一看,鼹鼠不见了,它去哪儿了?随着故事的发展,人们开始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老人们告诉他们,的确有一只奇怪的鸟飞过后就不见了,还有人记得他的曾祖父告诉他,很久以前的确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灌木丛里发出很吵的声音。很久以前是多久以前呢?是记忆的极限。因为记忆的极限在这里就是历史的极限。在此之前,什么都没有。在此之前,什么都不存在。历史是可以被记住的东西。
除了北部的伊斯兰地区,在非洲都没有文字,这里的历史是口口相传的传说,是在杧果树下不经意间创造出的神话,在深邃的黑夜中,只能听到长者颤颤巍巍的声音在讲述,因为妇女和儿童都在静静地聆听。这个晚间时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在这个时刻会思考自己是谁,从哪儿来,会意识到自己的特殊与不同,会确定自己的身份。这也是和祖先交流的时光,祖先们虽然已经离去,但一直在指引他们,保佑他们不受邪恶的伤害。
晚间树下的寂静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这片寂静中充满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和响动。它们来自四面八方,来自高高的树枝之上,来自周围的灌木丛之中,来自地下,来自天上。在这种时候,我们最好待在一起,彼此靠近,我们感受到他人的存在,就可以感受到慰藉和勇气。非洲人每时每刻都感觉活在威胁之中。在这片大陆上,大自然呈现丑陋凶恶的形态,戴上复仇的恐怖面具,为人类设下陷阱和圈套,让人们生活在不确定、恐惧和惊慌之中。在这里,一切都被放大了好几倍,以肆无忌惮、歇斯底里的夸张形式出现。如果这里有暴风雨,雷电会撼动整颗星球,闪电会把天空撕成碎片;如果下起倾盆大雨,一道坚固的水墙从天而降,顷刻间就会把我们淹没,把我们砸入地下;如果出现干旱,那么一滴水也不会留下,我们会被渴死。这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缓和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没有妥协,没有中间状态,没有循序渐进。一直以来,只有斗争,战斗,生死之战。非洲人是一群从出生到死亡都身处前线的人,始终与这块大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作斗争,他能活着,能生存下来,就是他最大的胜利。
傍晚时分,我们一同坐在大树下,一个姑娘递给我一小杯茶。我听着这些人的讲述,他们坚毅的面庞闪着光芒,如同乌木雕刻而成,融入了静止的黑暗之中。我不太能听懂他们说的话,但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严肃认真。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认为自己是要对本民族的历史负责的。他们必须将历史完整保留并继续发展。没有任何人能说,“你们去读一读关于我们历史的书吧。”因为从没有人写过这样的历史书,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书。除了现在在这里讲述的历史,其他历史都不存在。这里永远不会出现欧洲那种“科学历史”或“客观历史”,因为非洲的过去没有文件或记录,每一代人都是一边听着别人传授给他的版本,一边对这个版本进行修改,不断地改变、转变、修订和修饰它。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历史摆脱了档案的沉重,摆脱了数据和日期的严格要求,历史在这里呈现出最纯粹的、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形式——神话。
在这些神话中,所有日期和对时间的机械衡量——日、月、年——都由其他表述方式来代替,比如“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或者“久到没有任何人记得以前”。一切都可以根据这些表述来安置并排列在时间的层次中。只不过,这种时间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像我们的地球一样,匀速地旋转。在这样的时间观中是不存在“发展”的概念的,取而代之的是“持续”。非洲是永恒的持续。
天色渐晚,所有人纷纷回到自己的家中。夜晚开始了,夜晚是属于鬼魂的。比如,女巫是在哪里聚集呢?大家都知道,她们是在树枝上、藏在茂密的树叶后面召开她们的会议并进行讨论的。最好不要去打扰她们或者躲在树下,因为她们最讨厌别人偷听偷看。她们报复心非常强,一定会来报仇,给人类植入疾病、制造痛苦并传播死亡。
所以直到黎明,杧果树下都是空的。黎明时分,太阳和树影会同时出现在地面上。太阳把人们叫醒,人们会立即开始躲避它,寻求树荫的庇护。这很奇怪,但人类的生命的确依赖于像阴影这样短暂而脆弱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提供阴翳的树不仅仅是一棵树,更是生命本身。如果雷电击中树顶、杧果树被烧毁,这里的人们就没有地方可以躲避阳光,也就没有地方可以聚集在一起。由于没法聚在一起,他们将无法决定任何事情、解决任何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将无法讲述自己的故事,因为只有傍晚在树下聚会时,才能将这些故事口口相传。所以,他们很快就会失去对昨天的了解,失去对昨天的记忆。他们将成为一群没有过去的人,换句话说,他们将成为一群没有身份的人。他们将失去那些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他们将散去,各奔东西,形单影只。但是孤独在非洲是不可能的,一个孤独的人一天也活不过去,他注定会死。因此,如果闪电击碎了一棵树,生活在树荫下的人们也会死去。不是有这样一句俗语吗:一个人不可能比他的影子活得更长。
除了树荫以外,第二重要的就是水了。
“水是一切,”生活在马里的多贡族智者奥格特美力曾经说,“土地从水中来,光从水中来,血液也从水中来。”
“沙漠会教会你一件事,”一位来自尼亚美的撒哈拉游商曾告诉我,“有一样东西会比女人更让你渴望和热爱,那就是水。”
树荫和水,这两样东西都是流动的、不确定的,都是出现之后不知道何时何地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两种生活,两种境遇:每个第一次来到美国那种大超市或者无边无际的购物中心的人,都会被堆积在那里琳琅满目的商品所震惊,人们还会惊叹,在那里有人类发明和制造出来的一切物品,然后这些物品会被装车运走、打包堆好、摞高,让人觉得顾客不需要操心任何事情,有人之前已经帮他们把所有事情都想到了,现在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唾手可得。
而一个普通的非洲人的世界完全是另一副模样,这是一个贫穷的、最朴素的、最基本的世界,精简到只有几样物品:一件上衣、一个碗、一把粮食和一口水。这个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不是以物质、实体、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来表达的,而是体现在它赋予最普通事物的象征价值和意义,那些事物太普通了,以至于外人难以理解并且不易察觉。比如,一根公鸡的羽毛可以成为黑暗中照亮道路的灯笼,一滴橄榄油可以成为抵挡子弹的盾牌。最微小的事物都具有象征性和形而上的意义,因为人们就是这么决定的,他们通过自己的选择,将事物提升到另一个维度、另一个更高的领域——进入超然的存在。
由于欧洲语言的某种贫乏性,非洲生活中的很大一个领域仍然没能被深入了解,甚至没有被接触到。如何形容黑暗、绿色、闷热的丛林深处?成百上千种的树木和灌木都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一些植物的名字,比如“棕榈树”“猴面包树”“大戟属”,但这些树都不是长在丛林中的。那些长在乌班吉和伊图里、有十层楼高的参天大树叫什么?这里随处可见的、不断攻击和叮咬我们的各种昆虫叫什么?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找到一个拉丁语学名,但这能向普通读者说明什么呢?这还仅仅是涉及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那么关于这些人的心理、信仰和思想的巨大领域呢?每一种欧洲语言都是丰富的,但只是在描述自己的文化、介绍自己的世界时才是如此。当某种欧洲语言试图进入另一种文化的领地并进行描述时,就会暴露出自身的局限性、欠发达程度以及在语义上的无能为力。
在前殖民时期——其实这也并非很久之前——非洲曾有一万多个小国、王国、民族联盟和联邦。伦敦大学历史学家罗纳德·奥利弗在其著作《非洲的经验》(The African Experience,1991年于纽约出版)中指出了一个常见的悖论:人们约定俗成地说欧洲殖民主义者瓜分了非洲,“但是怎么能用‘分’这个词呢?”奥利弗非常不解,“这明明是用火与剑进行的残酷统一!从一万多个缩减到了五十个!”
但是,这种马赛克,这幅由石子、骨头、贝壳、木块、铁片和树叶组成的闪闪发光的拼贴画,其多样的元素还是保留下来了。我们越是仔细凝视,就越能看到画中的组成元素在眼前交换位置、变化形状、改变颜色,形成一个多变的、丰富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奇观。
几年前,我和朋友们在坦桑尼亚腹地的米库米国家公园一起过平安夜。那天晚上很暖和,晴朗无风。在丛林中的一片空地上,在开阔的天空下,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有炸鱼、米饭、西红柿和当地的自酿啤酒。我们点燃了蜡烛、灯笼和油灯。气氛轻松愉悦。有笑话,有笑声,还讲了很多故事,在非洲,这样的场合总是如此。那天一起过节的有坦桑尼亚政府的部长、大使、将军以及氏族首领们。凌晨十二点已经过了。我突然感觉到,一个厚重的巨大黑影在灯火通明的桌子后面摇曳着,发出咕咚咕咚的声音。没过多久,这个声音变成了轰隆巨响,而且很快就出现在我们背后,在深沉的黑夜中,出现了一头大象的身影。我不知道,你们之中是否曾经有人和大象四目相对,我说的不是在动物园或者马戏团,而是在非洲的灌木丛中,在这里,大象是世界上最危险的霸主。人们看到大象会吓得魂飞魄散。这是一只离群的孤象,这种大象通常是一个狂躁的袭击者,它会冲向村庄,踏平泥坯屋,杀死人和牲畜。
大象真的非常大,目光锐利,一言不发。我们不知道它硕大的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不知道它下一秒会做什么。它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始在桌子中间走动。桌旁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吓呆了,一动都不敢动。你不能跑,因为一跑会惹怒大象。而且它跑得很快,没有人能从大象面前跑掉。但如果就这么一动不动地坐着,你就暴露在它的正面攻击之下,这个庞然大物的腿随时可能把我们撵成肉饼。
大象继续溜达着,一会儿看看摆满食物的桌子,一会儿看看油灯,一会儿又看看忧心忡忡的人们。从它的动作看得出,它在犹豫,一直无法做出一个决定。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很久,久到看不到尽头,仿佛一切静止在冰封的永恒中。我在某个时刻捕捉到了它的目光。它认真严肃地看着我们,眼神中有一种深刻的、不可动摇的阴郁。
最后,大象绕着我们的桌子和空地走了几圈之后,丢下我们走开了,消失在黑暗之中。当重物砸地的轰隆声停止后,黑暗中一片寂静,一个坐在旁边的坦桑尼亚人问我:“你看到了吗?”“看到了,”我仍心有余悸地回答他,“一头大象。”“不,”他回答道,“非洲的灵魂总是以大象的形象出现。因为任何动物都是无法战胜大象的。狮子不行,水牛不行,蛇也不行。”
大家默默地回到了自己的泥坯屋之中,男孩子们吹熄了桌上的灯光。此时仍是黑夜,但是非洲最闪耀的一刻也越来越近了——黎明将至。
(本文节选自《太阳的阴影》中《在非洲,在树荫下》篇章,发表时有删节,标题为编者所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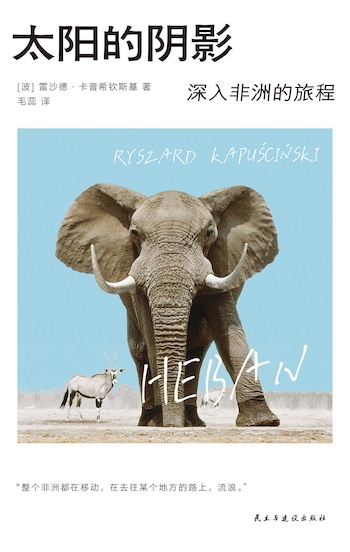
《太阳的阴影:深入非洲的旅程》
[波] 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 著 毛蕊 译
理想国·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25年6月
文章作者

中国稻种在塞内加尔:巧织雀与睡莲共舞,还能守护“大米主权”
在塞内加尔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道路上,来自中国的“绿色超级稻”正扮演着关键角色。

出海新变量|月均出口四万台设备,中国血糖仪企业叩开非洲市场
业务起步时充满挑战性。

非洲学者研究中国,除了基础设施还会关注哪些
赞比亚副总统纳卢曼戈邀请中国企业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框架,考虑赴非在医疗领域投资兴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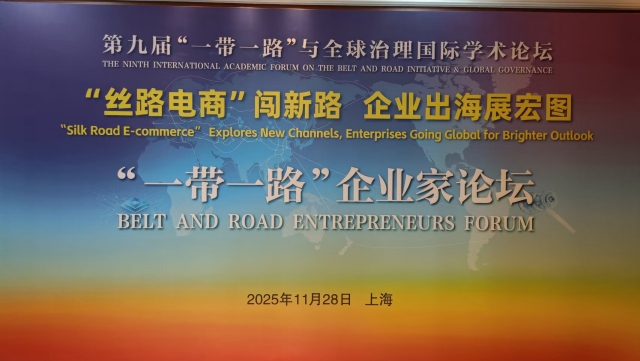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升温,企业家与学者怎么看
今年前10个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34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3%。

市面上有五万多种膳食补充剂,哪四种确实有效?
替代医学寄托着希望和念想,也可能成为资本和骗局的温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