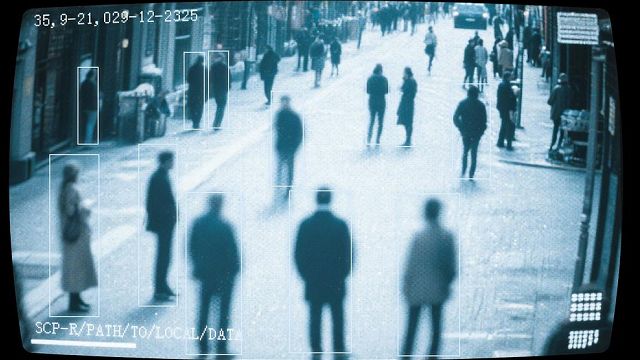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编者按:震惊一时的“出洋五大臣被炸案”,在三十篇日记中呈现出了怎样的不同面貌?曾国藩为何酷爱围棋,他的棋友都有谁?
中国自有文字诞生以来,即有按日记事的传统。宋代以来,日记作为日常书写和反映个体精神生活的一种载体,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新书《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通过八个专题,探讨清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并引入书籍史、情感史、饮食史等研究方法,令书写更为丰富立体。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自该书第三章《新年发笔与清代读书人的仪式感》。
新年发笔是读书人新年第一场集体性的文字狂欢,是一场信念、愿望、不安和勖勉的盛会。新年第一次书写的文字,不仅宣示了希望和祈祷,寓意了吉祥和祝福,也深层次地表达了自己的渴望、失落和旧时光里的遗憾。这些高度抽象的吉祥用语反映了普遍的志向、抽象化的理想,但这些程式化的用语也植根于日常生活和实际需求之间。一些文人变换用语,使用元旦试笔诗等方式,又使得这些文字形式变得多元。
在展望新年和未来美好愿景的同时,一些追忆往昔的新年发笔充满叹息,同样耐人寻味。现代著名文献学家陈乃乾(1896~1971)1959年日记开篇云,“年少鸡鸣方就枕,老来枕上听鸡鸣。转头三十馀年事,不道消磨只数声。黄梨洲句。己亥元旦试笔,时年六十又四”。陈乃乾现存16年的正月日记,所记试笔事唯此一处。对身处艰难时代的老人而言,新年发笔以叹息模式开启,并不令人意外,却也足够让人对新年发笔的多元化生出无限感慨。这些多元的特性使得新年发笔成为展示道德修养与文学技艺的一部分,文人不仅可将其用于表达通俗的愿景,也可用来表达个体微妙的诉求。
若仍将清朝视作“儒教中国”(Confucian China,Joseph R.Levenson语)链条上的一环,就不能不对清朝文人这种普遍性的元日书写活动做一些信仰上的解释。与传统中国的许多文人一样,清朝文人的诸多书写活动都笼罩于“文人信仰”之下。这种文人信仰的核心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附着其上的诸多文字,均可视作文人践履信仰的注脚。宗经征圣的文章、卫道明道的诗文,均可视作这种信仰的产物。新年发笔则再一次印证了这种信仰的力量,当其与民间习俗融为一体,便永久地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扎下了根。
传统的新年活动之中,祭祀、社交和娱乐等功能是最为突出的,新年发笔巧妙地在其中新增一类,将传统民俗材料转化为一种文人表达自我的手段,并内涵于个体书写之中。这种特殊的节日狂欢的个体实践,过去并不为民俗研究者重视。如今,我们将目光聚焦到节俗书写,日记无疑是民俗研究尤其是节日研究值得重视的“新文献”。
文人在表达祈愿和功利心声方面往往沉默不语,因而在许多时候缺席了日常的狂欢。关于文人如何参与庸俗的日常,研究者往往觉得无足轻重,或难于措手,因为文人在各种书写中有意“伪装”,形成事实上的沉默。从这个角度来说,材料的“沉默”仍是解读文人生活所需面对的严重问题,而日记似乎例外,通过它可以不断“穿刺”文人丰富的心灵世界,尤其是功利性的那一面。并置各种材料以打破文本自身的沉默,从而倾听文人世界应有的喧哗,是激活日记文献必需的尝试。作为文人心迹的碎片残留,新年发笔为这种尝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毕竟,新年发笔反复出现在文人日记中,多数并非文人的有意构建,而是日常心迹的无意流露。
从较小的时间单位如元旦出发,看待这时文人间兴起的活动,是探测文人心迹的有效手段。新年发笔既表现了普通人吉祥如意的心愿,也深层次揭露了文人的出处去就,甚至可作为检验读书人底色的重要标准。就日记所揭示的新年发笔内涵而言,许多文人终生行之,将新年发笔培育成持之以恒的人生兴趣。这是一种可贵的文人传统,是能识文断字的读书人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这种习俗从读书人(尽管起初来自中下层读书人)中逐步推广至社会全体,流风余韵绵延不绝,证明文字与文人本身具有深厚的力量。
在看似千篇一律、内容高度同质化的每一天,日记文本背后却微波粼粼,涌动的并非完全敞亮的世界与人心,表明日记作者的不少生活角落只是有限度地公开,如新年发笔这类新年间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日记中都只偶尔一现。窥探此类生活的角落,进入文人看不见的心灵世界,需要深度搜索、并置材料,撕开日记文本的包装,从而挖掘其内里峥嵘的头角。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新年发笔既是个人自誓行动的总要求,是自我暗示的行为指导,也表达了无意识的担忧和愿望。从这个层面而言,沟通神明与自省自励构成了新年发笔功能性的两端。故一般而言,为科举所压迫愈深的读书人,其人新年发笔的方式愈为丰富,体例更为谨严,在时间上也坚持更久,如萧穆、杨葆光等。而那些身处文化边缘地区的文人,往往能将新年发笔的传统坚持得更好,并更愿意在日记中不断重述这一传统,如郭嵩焘等人。
文人们一旦选择在日记中不断展示新年发笔,就难免暴露自己思想的底色。我们因而可以通过元旦书写的文字内容,推导写作者的心路历程,进而测绘其人的“文人性”。以杜凤治《望凫行馆宦粤日记》为例,日记所示元旦举笔的内容为“如意大吉”(同治七年)、“开笔大吉”(光绪三年)、“凡事如意,大吉大利”(光绪七年)等,颇显浮泛,并非反映为官为学方面的独特祈求。由此可见,杜凤治是一名合格的基层官员,却绝非一位坚定的文字信徒。
清代文人创造或拓展了许多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如新年发笔、寿苏会、消寒会、新年团拜等,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活动背后隐藏了许多关于个人与社会的问题。探究新年发笔这一充满仪式感的小传统,有助于我们重返历史现场,看看历史上的文人在新年这一天写了什么,为何而写。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认识到这一时期文人究竟面临着什么问题,社会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细碎但体量庞大的日记文献,以宏富的内容,自带了这些问题的答案。利用这些丰富的日记文献,有助于我们敏锐地把握清代以来充满仪式感的小传统,进而无意识地触摸并感知彼时一些问题的基本轮廓。
在一个仪式感日益缺乏的时代,在读书人越来越失去特殊信念与特定行为的年代,重温新年发笔的传统并非毫无意义。这是恢复日常生活仪式感的基础,也是重建日常生活仪式的必要铺垫。新年发笔这样充满仪式感的行为,看起来空洞无物、千篇一律、略显枯燥,然而本章对绍英等人元旦发笔内容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些内容虽然结构简单,却自具传统并带有仪式感,是一类充满波澜的模件化写作,是心灵希望和道德自省的外在体现。一个充满仪式感的文人群体是可以信赖和易于捉摸的。尽管不断累积充满仪式感的活动可能让这个群体和社会变得雷同,变得单调而枯燥,却也有助于让这个群体和社会变得易于理解,变得稳定且更适于沟通。
1941年元旦张道藩(1897~1968)致信蒋碧薇(1899~1978),开篇即云:“去年元旦发笔,是写信给你,今年还是写给你……”新年发笔的仪式感在最隐秘的私人情感中显示了郑重的意味,因而也增添了人情的厚度。从这个角度来说,恢复人们日常生活里的仪式感,不仅有助于完善个体的历史认知,也有助照亮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可爱之处。

《大清万象:清代日记中的情感世界和社会生活》
尧育飞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