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1913年,连续30多年保持年均增长3%以上(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人均GDP全球排名第10的阿根廷正憧憬着玫瑰色的未来。几乎每个人都认为,阿根廷迟早会追上当时排名第一的美国。但这没有成为现实。1964年,阿根廷的人均收入排名跌至第18名,2008年则是第28名。
2012 年, 中国正站在阿根廷的1913。给中国“算命”的版本不胜枚举:最乐观的“水晶球”来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他预测,中国将保持9%的增长直至2023年,此时,人均GDP将达到最发达国家水平的60%;此后,尽管经济增长率会放缓至5.5%,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倍。OECD的最新报告悲观一些,以购买力平价的不变价格计算,到206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美国的59%,此时,中国和印度将占据全球产出的接近一半。而IMF早先的估算显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在2016前后就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这些预测是否会成为现实?中国是否会重复阿根廷的命运?随着新一届领导人就位,全世界兴味盎然地注视着这个往往令他们匪夷所思的中国。中国最高决策者在2012年勾画的胸中蓝图(公布以及没有公布的),不仅将决定中国能否远离“阿根廷陷阱”,也将影响和重塑整个世界的未来。因此,尽管冒着成为陈词滥调的巨大风险,我们还是将2012年“第一财经-信诚年度金融书籍”的关键词定为:中国与世界。
在这个关键词下,我们选定了三本年度大奖书籍。其中两本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论中国》以及前文提及的萨勃拉曼尼亚所著《大预测》。别人眼中的自己,不免有些陌生,但却可能提供令人深思和警醒的不同视角。在外交层面,最有资格“论中国”的,莫属基辛格。而在涉及未来中国经济的几本书中(《邹至庄论中国经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下一次大趋同》),我们最终选定《大预测》,并非因为其预测最为乐观,而是因为看好本书的作者——作为华盛顿智库圈近年来冉冉升起的新星,这位相对年轻的印度人最有可能等到最远的未来,并亲眼看到自己的预测是否落空。
既然是中国和世界,还需要一本描述中国如何影响世界的书。在大国竞合的语境下,即便在危机后G20的框架和平台上,中国影响全球标准和决策的案例依旧微乎其微。周小川的文集《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与应对》是本不折不扣的学术著作,通读多篇首次公开的文稿,了解背景的读者会发现,全球经济金融的交锋,在最高意义上,是学术、理论和智慧的交锋——用西方世界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提出中国立场的分析和全球解决方案,在学术上站得更高,才可能赢得和中国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和尊重。而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高层决策者而言,还是一件非常陌生的事。
如同往年,“金融专业主义”依旧是我们的立身之本和“标签”,因此,利率市场化、汇率国际监督、操作风险、银行改革、政策性金融,这些可能让非金融专业的读者望而却步的书籍还是占据了我们榜单的主要位置。此外,我们还推荐了一本揭开货币和经济增长之间“致命关系”的著作《德国马克与经济增长》,对于人民币和中国的未来,这本书中高品质的第一手文献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验和借鉴。
推荐双语书籍,也是我们持续多年的习惯。除了大奖书籍外,两本双语书籍值得特别关注,今年六月任期圆满返回祖国的林毅夫教授的新著《繁荣的求索》、以及危机后最被关注的经济金融学家希勒(Robert Shiller)的新著《金融与好的社会》。前者是作者在华盛顿任职期间研究和心得的精华;后者则在金融声明狼藉的今天宣示,金融可以和美好的社会相连接,而非相反。
在经济学和广义经济学领域,我们的推荐书籍还包括宏观经济(连平的《跨越与转型》)、收入分配(王小鲁的《灰色收入与发展陷阱》)和能源(耶金的《能源重塑世界》)等话题。延续过往两年的兴趣,我们今年继续选定了两本经济金融和心理学交叉领域的新作——《思考,快与慢》和《The Hour between Dog and Wolf》。
在我们的榜单上,还有几本没有中文版的英文书籍,几位大名鼎鼎的作者包括:英国FSA主席特纳(Adair Turner)、索罗斯(George Soros)、罗格夫和莱因哈特(Carmen Reinhart and Kenneth Rogoff)。祝阅读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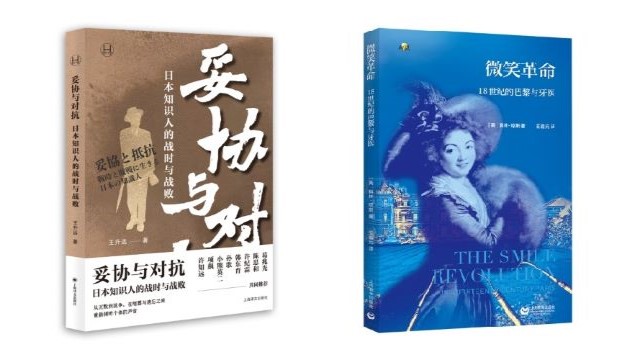
口腔医学的兴起和“微笑革命”的诞生|荐书
随着口腔医学的兴起和“牙医革命”的助力,各种修复技术的尝试和精美的陶瓷假牙的发明,才为“微笑革命”准备好了物质和身体的基础。

我在伦敦卖豪宅|荐书
这是房产经纪人麦克斯的工作日记,他在伦敦的豪宅交易市场浸淫了15年,而今他选择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以非虚构的方式讲述出来。

整形外科之父的传奇人生|荐书
“烹饪最初只是一门简单技艺,历经一个又一个世纪的精细化演变,如今成为一门深奥复杂的技艺。”

信息爆炸式增长的莎士比亚时代|荐书
莎士比亚之所以并不像他所生活的年代看上去那么古老,反而有时显得非常现代,很可能是因为那个时代的欧洲,就像如今的世界,也处于一个激烈的转型期。

阿波罗8号和它首次拍到的“蔚蓝星球”|荐书
《地出》照片诞生并向全世界传播之后,人类才对一种全新的宇宙观达成了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