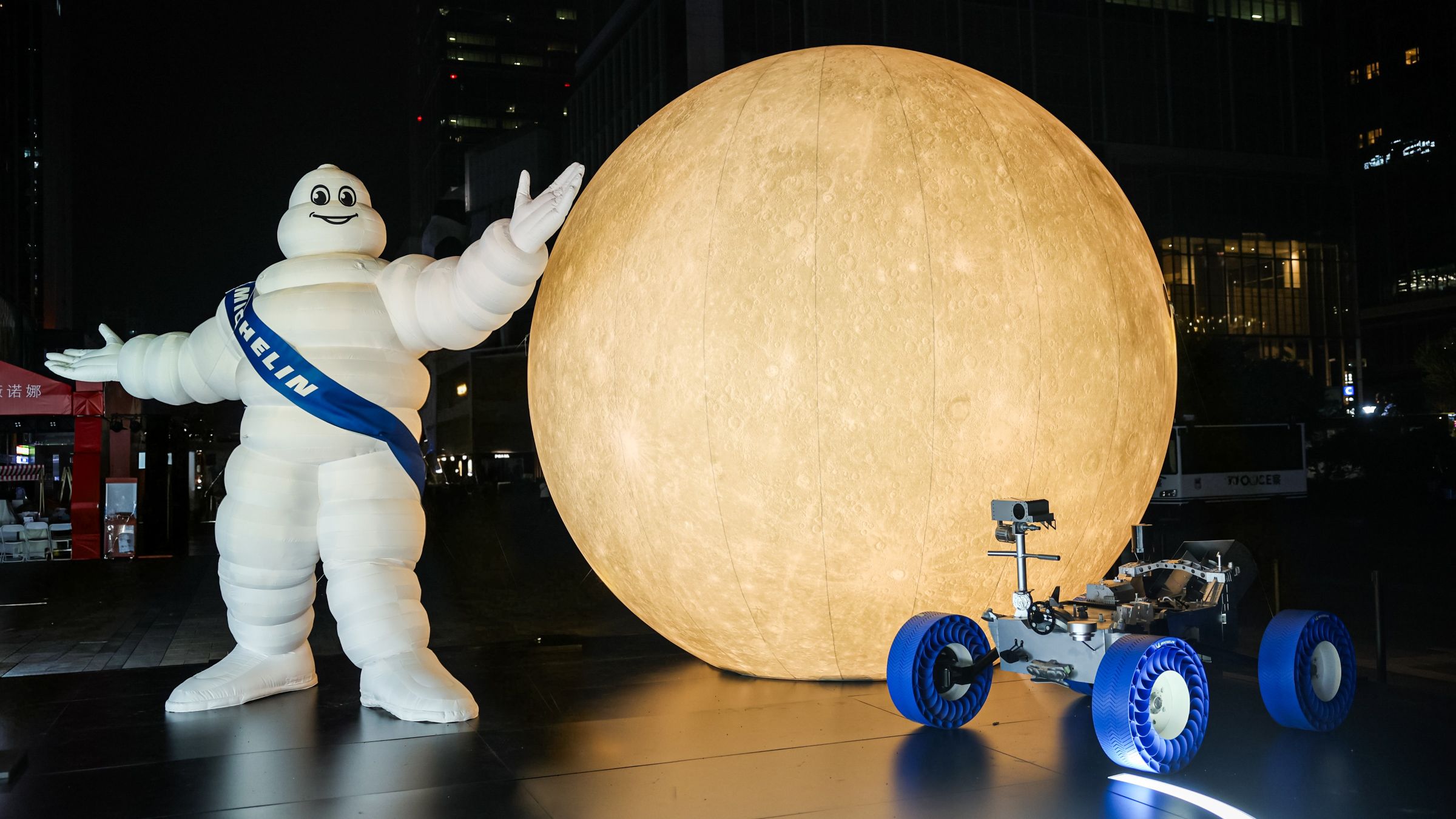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时间就是金钱,生命就是效率”。英国东亚问题学者马丁· 雅格斯(Martin Jacques)在研究中国人的“时间观”时发现,这个半个多世纪前被定义为“漠视时间的民族”,短短二十多年里生活节奏陡然加快。“全球城市人走路速度比10年前平均加快了10%,‘快生活’是全球性的趋势。而作为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都市人的‘快生活’竟然名列全球前茅。”
对于“快”的崇拜,让中国在改革开放后30多年时间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伴随着“快”而来的,一方面是金钱与物质财富的迅速积累,而另一方面,由“快生活”带来的焦虑、压力、躁郁、疲惫、惶惑等问题,成为都市人普遍的“心病”。就像印度谶语所说,我们的身体走得太快,是不是应该停下来等一等我们的心灵。然而,当很多人试图重新放慢生活的时候,却发现这并不容易,反而使得情绪负能量成倍增长。因为“慢生活”很可能意味着他不得不放弃原本唾手可得的金钱、权力、社会地位,以及社交资源,逐渐淡出主流社会。
我们真的已经慢不下来了吗?我们的“自慢”能力衰退的原因是什么?如何重拾这种重要的心灵自愈能力?上海复旦大学心理系主任孙时进,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详谈了他的看法。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大城市的生活节奏之快领先世界,而我们个人的“自慢”能力衰退亦很明显。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孙时进:从宏观层面来说,改革开放30多年,经济的进步使得中国有了向世界展现自己的能力,民族的历史悲情情绪正在慢慢淡去。但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中国人的自卑感、不安全感并没有随之消除,国民心态的转变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于是,“多”、“大”、“快”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追求。在这种追求的驱动下,我们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这种做法、这种追求,能增加我们的民族自信么?能让全世界接纳和认可我们么?结果,它们反而为我们带来紧张和压力,使我们的幸福感降低,同时也让世界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各国媒体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展开讨论就是佐证。
至于宏观层面的“快”如何影响到个人,目前在国内心理学界还没有专门的研究。而且,每个人进入“快生活”轨道、“自慢”能力的衰退,成因也大相径庭。我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人之所以感受到“快生活”带来的压力,产生负面情绪,很大程度上要追溯到童年的不完美。由于我们大部分人的童年都处于不十分理想的环境中,比如不受尊重,比如期许和结果不成正比,比如没有得到所期盼的自由、平等,这些问题对心理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童年时代的缺憾,导致心理不可逆转地缺乏安全感,焦虑长期伴随我们。而“快生活”则把这些问题暴露出来,让它们纠结成一股难以理清的乱麻。此外,整个社会信息变化加快,身边的物品总在不断更新换代,不停学习才不至于被社会淘汰,也成为人们“自慢”能力退化的根源。
日报:也就是说,从长远角度和宏观层面来看,让整个社会恢复“自慢”的能力,我们需要调整的是一种没有安全感的心态?
孙时进:是的。中国社会民众应该树立一种真正接纳自己的意识,客观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评价自己,完全接受自己,也适当地宽容自己。而政府治国理念则应该向着以提高民众幸福感为目的转变,给全社会每个人以尊严和生活的意义,促进个体的人格完整。而要让作为社会个体的人恢复“自慢”能力,情况就比较复杂,需要因人而异。
日报:说到个体,有很多有趣的现象。慢跑、手工艺、太极拳重新出现在都市人的生活中。一些人为了过“慢生活”,从都市“出逃”,去偏远小镇过“世外桃源”的生活。比如,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云南大理出现了一批都市白领。他们所采取的这些方式是否有效?
孙时进:我们讨论“自慢”问题,无非是想为人们在“快生活”的生活环境中,找到一种让心灵舒缓、平和,健康发展的途径。你提到的这些方法,只能起到一时的缓解作用,实际上,形式的改变无法解决内在的原因。就像电影《甲方乙方》中的故事一样,虽然有的人厌烦现有的生活状态,但是一旦离开,过上所谓的“慢生活”、“隐居生活”,又会因为焦虑而产生压力,反而走入一种回不去也不能前进的境地。
日报:也有人向往国外的生活,因为那里的人生活安逸富庶,“自慢”能力比国人强得多。他们认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熏陶之下,“自慢”能力似乎更容易恢复。
孙时进:我在宏观层面已经分析过,中国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的速度,与人们对心理的认知水准、心理承受能力的发展是不协调的。后者总是滞后的,这就产生问题。而像欧洲、北美、大洋洲的一些发达国家,社会的发展和人群的内在心理发展比较协调,而且心理咨询行业比较发达,所以他们的“自慢”能力、自我调节能力相对而言强一些。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逐步接近协调化需要漫长的过程。
另一方面,如果将恢复“自慢”能力一味寄托于移民、换环境,我认为有失偏颇。因为,没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对自我的未来需求没有清晰地认识,就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之,如果能做到认清自己的心理,从而进行自我调节就不需要离开现有环境了。
日报: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并不容易,这也是心理学上的难题。
孙时进:其实没人们想象的那么难。现代心理学有一种叫“内观法”的治疗方式,即对内在的自我觉察,进行相对应的调节。这种心理治疗方式,要求参与者通过回顾自己在社会中、人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比较现实和理想的差异,进行自我洞察、自我分析,以修整自己对生活、对工作、对人际关系的态度,消除不安全感,改善人格特征。
再则,内观疗法也是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它的观点明确,方式简便有序,极易掌握,也是一种自我协调心身的养生法。要恢复“自慢”能力的人,可以学习心理咨询的课程,用专业的科学知识进行自我观察和自我帮助。
日报:说到科学,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当科技发展为人类生活带来更多自由的时候,人类很多的心理问题也能够迎刃而解。
孙时进:很多时候,科技发展对人类而言就像一把双刃剑。对这个说法,现在还难以下定论。物质文明的变化产生精神文明的变化,这个社会才能真正改变。我个人则更倾向于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找智慧。
与西方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不同,中国传统哲学追求返身内求。尽管没有特定的心理学部分,中国传统哲学以天人合一观念为基础,用独特的理论阐述和精神修养方式,讨论四个关于心理的命题,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人与终极价值的统一。
儒家、道家在入世与出世两个相反的维度上巧妙地维持心理的平衡。佛教则站在超越性的立场,从彼岸看待现世,提供了与儒、道两家不同的审视人生的视角。中国传统心理健康思想的多维建构,保证了古时中国文人心理的弹性和平衡。这些传统哲学中隐藏着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对我们改变现在的状态依然很有帮助。
冯仑:所有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冯仑 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
地产商冯仑,自称为“悟道分子”。“我每天在琢磨,在反省,然后感知、表达。我不掉书袋,我也不是教书的,但又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他说。
这位著名商人常常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不是出书就是受访,再有时间就写博客、做播客、做电子杂志。依托他辉煌的创业史,还有那满满的书房,冯仑有了普通企业家所不具备的视角和观点,而他的时间观也与众不同。
冯仑把人的事业比作是马拉松,在每一个弯道处,大家的前后次序都会变化,但最终跑到底的是最有毅力的人,而不是某一段跑得最快的人。“最后的胜利属 于跑得最有毅力而又不跑错方向的人。一件事,一个公司,其价值往往并不取决于它本身,而是取决于它所存在的时间,生命力越久就越有价值。”他说,“所以, 一个伟大的人或者杰出的企业家,你要想拥有未来的事业,首先要对准备付出的时间在内心有一个承诺:一生一世,还是半辈子、三五年。”
冯仑藏书里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古书,是他从各处古董店、旧货市场淘来的,另外还有一部分怪书,讲黑夜、痛苦、死亡、资讯焦虑。他说自己有时候在晚上心 绪不宁时,就枯坐在书房里,既不能睡,也看不了一整本书,而无所事事到了极点,就会看看古书。“古书能很快让人安静下来。其他那些杂书怪书,想起来了就看 看目录,翻两三页,也能把平时思考的角度拉得更开。”他说。
对于冯仑而言,书的确是一个最佳的“慢”的介质。(钱梦妮)
麦葵:跨过快慢之间的那个围城
麦葵 夫妻档插画师、旅行绘本作家
广州插画师isolan麦葵夫妇现在的时光比从前远为悠长、细腻。而立之年辞职转为自由职业者之后,这对志同道合的夫妇如今以绘制插画维持生活。他们随时可以骑着自行车游走于广东的老城区,看下午三四点时,一个耐心品尝白斩鸡的大学生;看老爷爷老奶奶为春节备下的腊肉;与朋友聚餐;亲手种下植物。沉浸于这样悠游状态下4年,他们依然享受这样自由自主的状态。
其实,小麦和小葵并非天生散淡。与绝大部分大学毕业生一样,一出社会的时候总会有一番雄心壮志,却对获得“成功”所需支付的成本不完全知悉。大学毕业后,他们受雇于一家广告公司,生活日夜颠倒,随传随到,通宵工作是家常便饭。他们也想通过努力工作多多赚钱,但到后来,他们发现,自己的生活如一个陀螺一样高速转动,却依旧留在原地。焦虑感很快袭来:“我不知道自己为谁而工作,为什么要工作。也许,只有刚刚毕业的人能够承受。”做了好几年,他们看到,年资在这个行业的利益分配规则中则显得无足轻重,新鲜创意永远是最为关键的生产力。
恰在此时,他们画的插画逐渐在网上流传开来,积攒了一定的人气。两人决定辞去工作,专心画画。“我们觉得继续工作会让自己没有时间专注于自己的爱好,还不如辞去工作比较好。”
这对夫妇如今的生活节奏自然是缓慢多了,但他们眼中的“慢生活”也绝非碌碌无为。“慢生活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支配生活。这样才能潇洒、开心。”但同时,他们也同意,自由职业意味着更高的自律性。没有老板的催促、指标的压力,进取心来自对兴趣爱好的执着。
4年中,isolan麦葵出版了多部绘本。他们到泰国、厦门去旅游,将所见所闻一笔笔画出来,连同他们在广州的见闻汇集成“边走边画”系列。在泰国旅游时,服务生低声细语和慢条斯理给他们带来了触动。这是他们自己的生活风格。即便在广州,他们也能从身边发现慢生活的痕迹。
两人也为企业绘制商业插画,其间会有需要赶工或是被催稿的时候。但小葵认定:这时候的生活依然是由自己支配的,这就够了。浮华都市中各种财富传奇、贫富落差往往给人带来刺激。他们自言,不再会为之所动,因为:“做伴随一生的事业比高薪更为重要。”
“工作是一道围城。只是,我们出去了却从未想过再走进去。”他们说。(孙行之)
陈燕飞:有舍有得,学会“自慢”
陈燕飞 原创设计师,璞素家居品牌创始人
三年之前,陈燕飞辞去国内一家知名家居媒体的视觉总监的职位,走上了五味杂陈的原创设计之路。个人品牌璞素“阳春白雪”,而陈燕飞也很明白,“有舍有得”是他今天能够保持“自慢”状态的原因。
“现社会的价值体系,对成功的定义无非就是赚钱。在生活节奏加快的情况下,社会的压力和矛盾就会非常集中,导致人们的焦虑、惶惑、暴躁易怒。”他认为,想要改善这种社会状况,需要一种力量的正确引导。“西方发达国家的人‘自慢’能力相对强,那是因为他们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方式比较多元化。人们可以选择通过不同的工作,以及他们喜欢的生活方式找寻自己的价值,成就感、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除了经营设计之外,陈燕飞定时练习书法,每日笔耕不辍,闲时也会培养对于古乐、绘画、茶道、陶艺的爱好,或是到各地搜罗老家具,或是约上圈内一群好友喝茶、大啖美食。他对自己的生活没有那么多纠结,也没有那么多患得患失。对他而言,茶道、书法,既让他玩味技巧和气韵,也给了他独处、自省、内观的时间和空间;而搜罗老家具,用手触摸经历岁月沧桑的设计工艺和包浆,则给了他带来一种时间、空间交错的穿越体验。“这种结合了感官体验的感受给心灵带来的冲击和感悟难以言表,把生活和工作相紧密结合起来,既陶冶情操、滋养心灵,又能为工作带来新感悟、新思路。”
他始终认为,人不可能完全逃离现实。“生活在这个社会,受多方因素影响。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独善其身并非易事,但是只要你清楚自己到底需要什么,舍弃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慢慢摸索能让自己的心灵慢下来的方式,‘自慢’生活离我们并不遥远。”(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