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于2025年10月召开,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擘画蓝图。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根据会议公报,“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引擎,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深度融合,实现经济从规模扩张向质量跃升、从技术跟跑到创新引领的根本转型。这一战略部署中,新质生产力是动能核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实践载体,二者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的目标有哪些关键工作要做?如何理解在“十五五”时期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十五五”规划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在具体政策设计上,如何避免“内卷”,真正催生多元化的增量经济赛道?如何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第一财经对话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
郑永年的主要观点:
过去五年的科技投入已是质的不同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架构的根基 绝不能放弃、动摇
要拓展中国经济的外延 企业全球化就是“中国人经济”的体现
中国已处于“硬基建”向“软基建”过渡期
未来目标是民生为大 人才为大
“十五五”是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找确定性
中国已具备塑造自身国际环境的能力
发展增量经济有利于遏制“内卷”
政府需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系统工程
不仅要统一规则 还要改变对干部的考核要求
中国还有较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空间
未来十年还是需要5%左右的经济增速
适度放松监管释放经济活力
过去五年的科技投入已是质的不同
第一财经:郑教授好,您怎么看四中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这个目标,我们也注意到这是一个新的提法,这也显示政策层面重视科技的信号是很明确的,为什么这么说?未来我们有哪些关键的工作要做?
郑永年:我个人觉得这个当然是一种新的提法、新的概念。这里面首先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信心问题怎么来的?实际上我是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也是来自于“十四五”。
“十四五”其实我们走得是不容易的,经历了新冠疫情,特朗普开启了中美贸易战,然后出现脱钩、卡脖子、拜登(小院高墙)。那么这使得我们的科技投入已经不是量的变化,完全是不同的思维方式了。我们就是要用举国体制投入科技创新,对高科技的认知也深化了,完全是跟以前的性质不一样了。
人家卡脖子了以后你自己必须做了,而且要突破,你必须投入。那么“十四五”在各个方面,尽管我们也不太说,但实际上也是在科技上有很多的突破。这就给了我们一个信心,就是为“十五五”打下了基础,就是为什么“十五五”刚才你说的表述非常重要,我们要上一个台阶。下面的5年非常重要,就是“十四五”到“十五五”到“十六五”结束,相当于要2035年了对吧?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然后才有全面社会主义现代化。
四中全会公报为何没有提金融?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架构的根基 绝不能放弃、动摇
第一财经:您怎么理解在“十五五”时期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我们发现公报里面这一句话也是一个新的提法,同时还提到要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接下来要怎么做?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郑永年: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十八大以后,尤其是二十大以来,中国的决策者顶层设计,整个的政策跟以前不太一样的地方,就表现在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
实际上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就是一个主体。以前,科技创新是放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前面的,现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总体构架,它告诉我们什么叫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怎么做。
有一个同志提出来了,为什么(四中全会公报)没提金融?我是觉得“十五五”规划最终也会提的,但是这次没有提,实际上我们走对了。这些年我们一直是以实体经济制造业,尤其是高端制造业(为主),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强调创新,非常强调创新,但是你一个国家的创新,最终还是要反映到制造业里面,所以制造业是一个国家经济构架最基本、最根本的东西。
比如像我们觉得制造业是中国现在最有比较优势的。因为我们从最高端的到最低端的都有,我们中国是唯一一个联合国工业统计部门统计中制造业最齐全的。那么高科技,我们还是在追赶,有些地方赶上美国了,甚至有些地方可以超过美国了。所以这一块绝对不能放弃,绝对不能动摇。
现在经济学界你也知道一直在争论,我们消费不足。我个人觉得你要提高消费的话,还是要通过发展。怎么发展?我觉得还是实体经济制造业。这背后的逻辑要搞清楚,还是要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来提高消费水平。
中国已处于“硬基建”向“软基建”过渡期
未来目标是民生为大 人才为大
第一财经:《公报》里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想请教一下您为什么目前我们要如此重视民生,这对我们的国家财政和财力实际也是提出了更大的要求的,您怎么看这个提法?怎么实现可持续的民生的投入?
郑永年:实际上人民至上,人是目标。以前投资于物,现在投资于人,你也可以理解,这些年我们在做一个软基建这样一个大的课题。因为我们的硬基建已经投资非常好了,公路、桥梁、高铁。我们的硬基建的投资空间,我个人觉得也不大了,所以投资于物现在转移到投资于人,这是一个大的转型。
现在对人的投资的话,就要跟我们的高科技发展一定要关联起来。科技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人的竞争,就是人才。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就是它的核心。教育的目的也是人才,科技的中心也是人才。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消费,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你经济发展也好,科技发展也好,你到底为了什么?所以民生为大,所以民生非常重要。
西方出现问题了,美国我刚才说了经济发展、科技都没有问题,但是社会出现问题,就是民生出现问题,中产阶级萎缩。所以我是觉得对民生问题的强调,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因为这是你的目的,就是民生,就是人,就是人民至上。
要拓展中国经济的外延 企业全球化就是“中国人经济”的体现
第一财经:在各部委解读《建议》的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部长表示,“十五五”期间“既要重视中国经济,也要重视中国人经济”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在一个整体世界经济比较低迷的背景下,您觉得应该怎样同时做好中国经济和中国人经济?
郑永年:这里面的深刻意义是蛮大的。就是说外延,我们一定要拓展中国经济的外延。我们以前早期有一些片面的理解,就是我们企业走出去是不是就是资本外流?但实际上我们现在是比较正确的认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到这个程度,企业的国际化、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
企业全球化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的经济了。你到了东南亚、到了中东,到了拉美,这是互相强化互相促进的。你一定要拓展经济的外延,我是觉得有一点哲学,但是确实也是正在发生的。
“十五五”是在不确定的国际局势中找确定性
中国已具备塑造自身国际环境的能力
第一财经:未来5年中国发展面临的这些国际形势中,您觉得比较确定的是哪一些?不太确定的又可能是哪一些?中国在5年规划中,应该怎样去准备和应对这些确定性和不确定性?
郑永年:有确定性,也有不确定性。我个人觉得“十四五”真的不容易,那么多的东西都没有预料到。“十五五”的话,我觉得反而有点确定性了。所以从中美关系来说的话,当然特朗普是不确定的,但特朗普在位上是确定的,我们很熟悉他的套路了。所以基本上我当然觉得到中美关系尽管是不确定的,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觉得这也是确定的,好多东西已经都暴露出来了。
但是我们国内是确定的。我们的基础,我们的制度优势是在的。实际上我们对我们“十五五”规划要做的,反而更加确定了。所以我觉得“十五五”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更坏的情况,但是我们心里来说,我们政策上准备更充足了。我们现在是已经有能力来塑造我们自己的国际环境。不仅来塑造我们的国际环境,像对等的稀土新规,我们也可以为美国塑造国际环境,所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是有定力来对付黑天鹅,不管你出现什么,这一点是很重要。
发展增量经济有利于遏制“内卷”
政府需要在体制机制改革上下功夫
第一财经:您指出中国经济的“内卷”源于新的增量经济活动不足,而非存量竞争本身。“十五五”规划将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突出位置,您认为在具体政策设计上,如何避免各地在少数新兴领域“一哄而上”,真正催生多元化的增量经济赛道?
郑永年:几个层面:一个就是要禁止企业做什么?现在反内卷,现在国家层面也在考虑价格法,你不能无限降价,造成通缩,太内卷。但是我是觉得还有一个政府应当做的,就是发展新的产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直想推动我们的游艇产业发展,我们的海岸线那么长,游艇产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为什么不让他做?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其实跟以前的日韩差不多,前面几十年都是西方技术的应用扩散,但是二、三十年的积累以后已经转向了原创。但是原创技术要落地的话,生产关系、体制机制某一部分的层面上就要改革,所以还是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这次也强调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这一块也是需要行政、体制机制改革。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系统工程
不仅要统一规则 还要改变对干部的考核要求
第一财经:建成统一国内大市场是“十五五”的一个重大任务和目标,您之前多次也强调了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通过建设统一的大市场释放内部的潜力,结合“十四五”期间的实践,“十五五”在推进区域大市场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连接当中,应该如何平衡地方利益和全局的布局,防止出现新的这种市场分割?
郑永年:实际上我的理解就是你要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就是规则规制的统一。正因为各地的规则不统一,大家恶性竞争。以前还有土地很多的优势,现在的话这些优势就没有了。内卷的结果使得地方债务越来越多,但无非就是我给拉企业,我给你税收返还。地方政府对内卷也是深恶痛绝。
所以全国统一大市场我个人觉得是个系统工程。它不仅要统一规则规制,比如说广东的招商跟湖南的要统一起来。还要改变的就是对干部的考核。如果对干部招商引资还是一个考核标准的话,他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竞争,就陷入恶性竞争。竞争一定会有的,肯定会有的,迫使地方政府要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这样的良性的竞争,这样才会促进经济发展。
中国还有较大的技术创新和产业空间
未来十年还是需要5%左右的经济增速
适度放松监管释放经济活力
第一财经:我们提出要在2035年我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业内专家测算,要达到到2035年要达到这个水平,我们的 GDP这10年中间还是要维持在5.5%-6%这样的区间。想问一下您觉得预测是否合理,我们有哪些因素或者优势可以继续保持这样的增长?
郑永年:我个人觉得首先怎么看GDP。因为GDP如果你要从国际来说的话,有汇率好多方面的各种的因素,我是觉得5%左右还是需要。
我以前写过文章,就是我们现代产业体系,大国的现代产业体系有5个“一定要”:一定要全、一定要大、一定要多、一定要密,一定要强。现在如果房地产走到顶了,或者其他以前的传统产业走到底了,你就要释放出新的产业。
不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创造新的产业,实际上我们有大量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的新技术。所以这一块就是说还是要改革,体制机制的改革。我觉得我们的监管,有些地方该监管的就监管,不该监管的要适度放松一点。
像技术落地,转化成具体的经济活动,实际上我们面临很大的挑战。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监管部门更需要考虑最新的技术出现,你要考虑到我们要释放出更多其他的经济活动,否则就会出现社会问题。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何伟文:美国“唐罗主义”对中国有干扰、有冲击 但中拉合作前景不会变|首席对策
特朗普政府在拉美大搞“唐罗主义”,引发西半球贸易合作风险上升。近期,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旗下子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PPC)合同违宪,对此,中方表示将坚决维护企业权益。然而,随着西半球贸易合作风险的上升,对于出海企业,尤其是已深耕拉美市场几十年的中国企业,可能需要更谨慎地制定战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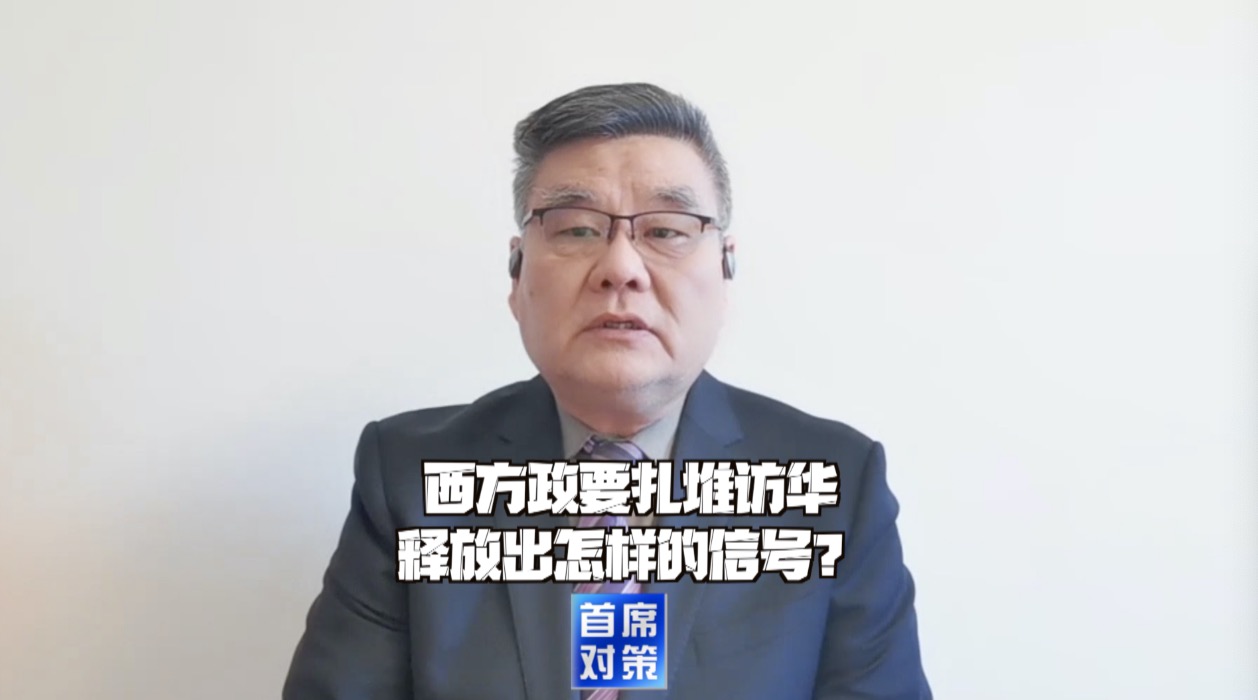
西方政要扎堆访华:是经济现实还是地缘觉醒?|首席对策
今年中国春节来得晚,给足了欧洲国家领导人扎堆来华的时间。从最早的马克龙,到刚刚离开中国的斯塔默,再到已吹风2月底将访华的德国总理默茨,短短两个月时间,欧洲E3国家领导人,将集中完成中国之旅,切莫说这中间还穿插着韩国总统、芬兰总理、加拿大总理。而这一不同于以往的局面到底意味着什么?《首席对策》专访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带来深入解读。

陶冬:黄金一旦调整会有一定幅度 但上涨逻辑未变|首席对策
2026伊始,全球经济已身处风暴。黄金狂飙,快速升破每盎司5000美元关口,并最高触及5598.75美元/盎司,之后急转直下,出现剧烈调整。国际金价暴跌达到12%,白银跌幅单日跌幅也创出历史新高。一系列正在进行中的国际秩序重构,以及跨资产类别的剧烈波动,让市场在亢奋与不安中交织。

美元全球大循环逐步走向衰落 中国当务之急是做强内循环|首席对策
在美元指数下破100大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关口之际,全球货币体系的多极化发展成热点话题。业内普遍认为,美元主导地位正步入边际弱化的长周期,人民币汇率温和升值概率较大。而以美元为主导的全球大循环已步入衰落阶段,但这一转变主要源于美国自身的经济结构与政策选择,而非来自外部的挑战。

作为履约守信底线 个人征信可修复透露了什么信号?|首席对策
12月22日,央行一早重磅发布《关于实施一次性信用修复政策有关安排的通知》。通知明确,对于2020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单笔金额不超过10000元人民币的个人逾期信息,个人于2026年3月31日(含)前足额偿还逾期债务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将不予展示。个人无需申请和操作,“免申即享”,支持信用受损但积极还款的个人高效便捷重塑信用。 这份《通知》被招联首席研究员、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是打破“一朝失信终身受限”困境、改变“破罐子破摔”想法的颇有诚意的举措,对于促进社会包容和谐,提振消费以及改善银行质量都有推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