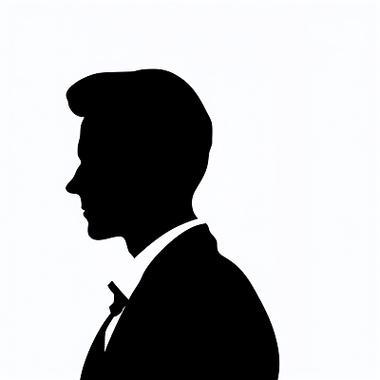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去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国宏观政策出现两大转变,即财政政策明显加力和政策重心转向消费。受此带动,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国消费市场明显回暖,以旧换新相关商品消费尤为亮眼。不过,今年7月开始,由于补贴规模减少、透支效应显现以及基数抬升,消费下行压力已经开始显现。
在笔者看来,消费总量指标的变化固然重要,但结构性分化亦不容忽视。本文梳理总结了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出的七大结构性分化,一方面提示当前消费增长面临的问题堵点,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未来消费发展的潜力所在。
分化一:商品消费改善,服务消费放缓
去年四季度以来,中国消费市场最为明显的一个趋势分化是,商品消费在以旧换新等政策带动下触底回升,而服务消费增长步伐逐步放缓,两者之间的增速差距明显收敛。
今年1-8月,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4.8%,较去年全年3.2%的增速大幅提升,主要得益于家电、办公用品、家具、通讯器材等以旧换新相关品类的拉动。居民人均商品性消费支出增速也从去年三季度的2.2%一路攀升至今年二季度的5.9%,这也是2022年四季度以来的最快增速。
相比之下,服务消费虽然保持一定增长,却显得有些“后劲不足”。1-8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1%,明显低于去年全年的6.2%。从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来看,增速也从去年四季度的6.9%持续回落至今年二季度的4.4%,是2022年四季度以来首次低于同期商品性消费支出增速。这一分化既反映了以旧换新政策的积极作用,也揭示了接下来提振消费的关键所在。
分化二:高端消费降温,平价消费受追捧
近年来,国内高端消费势头趋弱,注重性价比的日常消费则韧性十足。这种分化现象在白酒、汽车、餐饮等多个领域均有体现。
在白酒市场,以往备受追捧的高端品牌明显降温,以茅台和五粮液为代表的高端白酒市场价格较上年末大幅下滑约10%-2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定位更贴近日常消费的汾酒价格稳中略升。上半年,在白酒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明显放缓的背景下,山西汾酒的营收保持5.4%的增长。
汽车市场呈现出相同趋势,豪华汽车销售增速显著弱于平价汽车。1-8月,价格在15万元以下的平价车型销量同比增长近18%,表现强劲;而100万元以上的豪华车型销量同比大幅下滑近20%。
在餐饮行业,中高端餐饮倒闭、关停、降价、调整业务模式等消息频出。例如,去年10月以来,老牌米其林中餐鼎泰丰陆续关停了其位于北京、天津、青岛、西安、厦门、宁波等地的多家门店。1-8月,全国餐饮收入同比增长3.6%,而限额以上单位(年主营业务收入200万元以上的餐饮业企业)餐饮收入仅增长2.8%。
分化三:国产商品崛起,进口商品遇冷
伴随国产品牌的产品质量、设计创新、服务体验全面提升,中国消费者将更多目光投向国产品牌,“国产不如进口”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越来越多的行业都出现了“国货崛起、进口遇冷”的现象。
根据贝恩公司发布的《2025年中国购物者报告,系列一》,2012年以来,本土品牌始终表现出色,不断抢占外资品牌市场。到2024年,本土品牌整体市场份额已从2012年的39%攀升至76%。2024年,在报告追踪的27个品类中,有将近一半的品类出现本土品牌抢占外资品牌市场份额的局面,包括衣物洗涤用品、彩妆、卫生巾、洗发水、婴儿纸尿裤、冲泡咖啡等。
以服装行业为例,近年来,本土品牌的崛起重塑了中国服装行业的市场格局。根据中国服装协会、欧睿国际等机构统计,2024年第三季度,本土服装品牌的市场份额已达到45.6%,较去年同期提升3.2个百分点。本土品牌在运动服饰行业前20大品牌中占比约60%,安踏、李宁等头部企业持续扩张。
分化四:一线城市消费增速低于其他线级城市
2024年,中国消费市场呈现区域分化态势,一线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明显低于全国水平。今年以来,消费市场的区域分化仍在延续,一线城市社零增长持续乏力、大都低于全国水平。
一线城市消费疲软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比如房价下跌的负向财富效应更显著、受裁员降薪的冲击更大、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更多、部分城市常住人口减少、社会集团消费走弱、企业跨区域设立经营主体增加以及统计方面的因素等。尽管很难区分哪个因素更为重要,但提振一线城市消费的紧迫性越发凸显。
8月18日,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强调“系统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这对于一线城市消费回暖意义重大。近期,北京、上海、深圳的住房限购政策、公积金贷款政策出现不同程度放松,后续应还有进一步优化空间。
分化五:社会集团消费表现弱于居民消费
近年来,以政府和企业为主的社会集团消费表现偏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居民消费和社会集团消费组成,其中社会集团消费的占比大约在三到五成,对于零售大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2023年二季度开始,包含社会集团消费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持续低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社会集团消费疲软是造成这一分化的重要原因。
不同机构的估算也侧面印证了这一推论:中金公司计算显示,疫情之后(2020-2023年)社零增长疲弱,主要受社会集团消费拖累;中国银行研究院测算也显示,2022年以来社会集团消费增速开始低于居民消费增速,2024年进一步跌至负区间,是近两年消费的重要拖累因素。
分化六:低收入群体消费表现弱于高收入群体
一些电商平台消费大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低收入群体消费增速偏低,高收入和中高收入群体保持较快增长,且两者差距有扩大的迹象。
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分化的背后与收入差距扩大密切相关。2024年,从五等份收入分组来看,20%低收入户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最慢且下降最为明显,增速只有3.5%。今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3%,而收入中位数同比仅为4.8%。平均收入增速高于中位数增速,通常意味着收入分配更多向较高收入群体倾斜。
农民工收入状况也反映出类似问题。今年上半年,农民工月均收入增长同比降至3.0%,与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增长(5.0%)的差距达到2个百分点。而在疫情之前,这一差距通常小于1个百分点。
分化七:消费总量指标回暖,但消费信心指标低迷
去年四季度以来,反映消费总量的“硬数据”(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明显回暖,但反映消费信心的“软数据”依然维持弱势:
上半年,居民消费倾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5.5%,不仅略低于去年同期的65.6%,更比疫情前2019年同期低了2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为60.8%,比疫情前2019年同期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一些调查指标进一步佐证了消费信心不足的现状。7月,国家统计局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9.0%,连续28个月运行在90以下。其中,就业指数为72.8%,仍徘徊在历史最低水平。中国人民银行二季度城镇储户调查报告也显示,倾向于“更多消费”的居民占比降至23.3%,是2024年以来新低,而倾向于“更多储蓄”的居民占比为63.8%,处于历史第二高点。
“硬数据”和“软数据”之间的分化意味着,去年四季度以来的消费回暖主要依靠刺激政策驱动,居民消费信心尚未出现实质性改善。
政策层面如何应对?
面对当前消费领域的分化及其背后的制约因素,政策层面在积极应对。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在扩大商品消费的同时,培育服务消费新的增长点。在保障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需求”;8月18日的国务院第九次全体会议强调“持续激发消费潜力,系统清理消费领域限制性措施,加快培育壮大服务消费、新型消费等新增长点”;9月16日,商务部等九部门对外发布《关于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政策措施》。此前,贷款贴息、育儿补贴、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等多项惠民生促消费措施也陆续落地。
笔者以为,为扭转消费分化局面、推动消费持续改善,政策层面还需进一步加码。短期来看,可以考虑在扩大以旧换新覆盖品类的基础上,加大财政资金对服务消费的补贴力度。同时,鼓励和发展以游艇消费为代表的中高端消费,挖掘消费潜力;中长期来看,还是要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例如社保体系改革、户籍制度改革、收入分配改革等,将政策重心进一步转向消费、将资金资源更多投向民生和社会保障,以更可持续的方式支持消费提振。
(沈建光系京东集团首席经济学家、姜传钺系京东集团高级研究员)

供需两侧发力促“十五五”服务消费扩量提质
未来五年将是我国服务消费快速扩量提质的历史性跨越阶段。

“中国线上消费品牌指数”同比继续增长,女装、运动户外等行业品质升级加速
最新“全球品牌中国线上500强”季度榜单发布,真实消费指标为品牌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沈建光:四季度消费 “冷暖不均”,政策还需加力
商品消费走弱但品类分化、服务消费韧性较强、城镇消费明显放缓。

11月经济新动能表现强劲,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
实现全年经济目标有较好条件。

内需主导成核心抓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锚定2026年经济增长新路径
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作为首要重点任务,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正从出口导向向内需驱动转变,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