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今年乌镇戏剧节的“顶流”并非哪位明星,而是一个造型怪诞的“鸟人”。
鸟人是一个身形巨大的木偶,在操偶师的调动下被赋予完整灵魂,像是活了数百年的神明,眼睛却富于童真,好奇地张望着人类世界。它修长的手指握着一根绿色羽毛,轻抚运河边的杨柳、路过的工人,也邀请游客跟随律动起舞。在蒸汽朋克风格乐队的即兴伴奏中,鸟人转着圈摆动身体,撒下漫天羽毛,狂欢的气息在人群中迅速蔓延。像是童话世界的角色闯入了现实,又将现实变成了梦境。

这是第12届乌镇戏剧节古镇嘉年华单元的巡游节目《鸟人和它的奇美拉乐队》,来自法国剧团“明天改变一切”。现场观众拍摄的“鸟人”在短视频平台迅速传播,为乌镇戏剧节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很多游客专程为他而来。
10月22日是“明天改变一切”剧团在乌镇停留的最后一天。剧团离开前夜,Eric和三位朋友专程从苏州驱车赶来,这是他第一次参与乌镇戏剧节。尽管没有抢到戏票,但古镇上的巡游表演已足够让他不虚此行。Eric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他在社交平台上刷到“鸟人”视频后感到新奇,一通电话便约上了好友前往。
剧团的两场谢幕演出,他们都没有错过。“人多到夸张!”Eric感叹,“我们原以为工作日人不会太多,没想到这么火爆。幸好我们到得早,占到了不错的位置。”他有些不好意思地笑着:“虽然也没完全看懂,但还是看进去了,蛮值得的,以前从没见过这样的表演。”一旁的女孩轻声说:“他(鸟人)的眼睛很优雅。”
艺术,平等拥抱每个人
入夜,鸟人静卧在白莲寺外的走廊,仿佛睡去。晚风轻轻吹动它宽大的衣摆,如同呼吸起伏。有游客远远拍下它休憩的模样,不忍惊扰;也有人走近细看装置的细节,与艺术家轻声交谈。在社交平台上,甚至有手艺人缝制了缩小版的鸟人,造型纹理与原版一模一样。一场在地演出,因社交网络的传播,影响力呈倍数放大。
今年的古镇嘉年华单元,“明天改变一切”剧团带来的另一作品《吆喝火人》同样吸引了大量观众。以外,多支国际剧团受到欢迎。法国“走调剧团”带来的《喇叭筒之声》,以其灵动自由的表演吸引了许多观众。几位艺术家用自制乐器为生灵与万物演奏:花草树木、池中小鱼、酣睡的婴儿、搬运垃圾的工人……剧团谢幕演出的傍晚,艺术家乘着小船驶过古镇水巷,夕阳余晖为他们的演出布光,美妙的乐音随水波流入观众心中。沿岸人群安静聆听,与他们作别。

事实上,自创办之初,古镇嘉年华便与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共同构成乌镇戏剧节的重要单元。它以街头为剧场,倡导人人参与,让戏剧触手可及。今年几支出圈的剧团在表演方式上不谋而合:融合装置、音乐、巡游等多元形式,注重即兴与互动,在演出中不断制造惊喜,邀请观众沉浸其中,感受快乐。
文化乌镇运营经理兼乌镇艺术团副团长杨端晨负责嘉年华单元的剧目邀约与落地。谈到“鸟人”的火爆,他也非常兴奋:“他们的演出调性轻松自由,为观众营造出如梦似幻的体验,唤醒人们对快乐的感受。过去我们看到的偶戏可能只是单纯的操偶表演,而‘鸟人’结合了故事、音乐、即兴演奏甚至烟火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让所有人‘玩’在一起。我们预感到它会引发讨论,但火爆到这种程度,确实出乎意料。”
杨端晨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嘉年华单元每年收到五六百份报名申请,近年来一个显著趋势是,贴合公共空间与环境的演出越来越多,比如去年出圈的“漂浮歌后”和今年的“鸟人”。剧目选择也更倾向于包罗万象的跨界创作:“早几年可能更多是剧场式、镜框式的表演,如今艺术家更愿意结合空间与环境进行跨界尝试,可见戏剧本身也在不断发展。”
马拉松五联剧,仅此一站
有与民同乐的狂欢,也有专业的深度交流。在“鸟人”结束乌镇演出的同一天晚上,戏剧节开幕大戏《人类之城马拉松剧》(下称《人类之城》)的第二轮演出在乌镇大剧院落幕。剧院内,欢呼与掌声如潮水般涌动,演员们多次返场谢幕。
由德国导演卡琳·拜尔、剧作家罗兰·施梅芬尼与汉堡德意志剧院联合创作的《人类之城》是一部雄心勃勃的作品。全剧分为五个章节,总时长约9小时。作品重构了欧洲文明史上的著名神话——忒拜城的建立与覆灭,用当代语言重述古希腊悲剧,借由这个在暴力与冲突中缔造文明的故事,叩问人类命运,为今天的世界带来思考与启发。该剧在叙事、装置与表演等多个层面实现突破,问世以来几乎囊括了德语戏剧领域所有重要奖项。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之城》此前从未以五联剧形式在汉堡以外的城市上演。卡琳·拜尔透露,尽管多个戏剧节艺术总监曾发出邀请,但唯有乌镇将其变为现实。回忆起引进历程,文化乌镇副总经理潘杭感慨万千。作为特邀剧目单元负责人,《人类之城》是他接触过人员规模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作品——150余名剧组成员,相当于一次性引进五部剧目。
潘杭向第一财经透露,《人类之城》并非单纯的引进项目,而是一次中德团队的共创。导演在剧中启用了一支编制庞大的鼓队、一支歌队,并需要多名儿童演员。“如果全部从德国过来,成本过高。”今年年初,戏剧节派出年轻导演赴德学习,考察鼓队、歌队和儿童演员的构成与排练方式,沟通人员配置、年龄结构乃至鼓的数量与材质等细节。潘杭介绍,舞美布景及道具方面,部分从德国运来,部分则由本地制作,“忒拜城的黄金墙、大台阶等就是我们制作的,因此这也是不可复制的‘乌镇版’《人类之城》。”
《人类之城马拉松剧》最后一章《安提戈涅》落幕之后,潘杭注意到,许多观众留在乌镇大剧院大厅,兴奋地讨论剧情细节,久久不愿离去。在7天内,《人类之城马拉松剧》总共吸引了超过1万名观众走进乌镇大剧院观演。“一切都是值得的,”潘杭觉得,这次马拉松式的观演对中国观众而言,也是一次独特而重要的体验。
用文化留住人心
自2013年创办以来,乌镇戏剧节持续创新内容,每隔两三年便实现一次扩容:从最初的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小镇对话,逐步拓展出戏梦粮仓、戏剧集市、起跑戏剧等新单元。这些单元围绕戏剧的构思、创作、演出、评论及相关生活方式展开,让不同背景的游客无论是否走进剧场,都能沉浸于戏剧的氛围中。
杨端晨这样形容乌镇戏剧节的单元设置:“从入门到专业,每个单元都有适合不同人群的内容。”在他看来,仍有许多人从未接触过戏剧,正如今年许多因嘉年华巡游而来的游客,此前既未参与过戏剧节,也未进过剧场:“但只要被某场演出吸引,他们就有可能进一步了解戏剧,从陌生到欣赏。”
潘杭自乌镇戏剧节元年便参与其中。他认为,戏剧节根植于乌镇的独特环境与文化土壤。“在最传统的江南水乡上演最当代的戏剧,本身就充满张力,观众不仅欣赏,更觉得‘好玩’。我们每年都在寻求变化,将优质和丰富的内容植入旅游场景,这正是乌镇的与众不同之处。”
随着乌镇戏剧节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因疫情中断的国际观众也开始回流。今年,多位欧洲戏剧节艺术总监组团前来——毕竟《人类之城》全本仅在乌镇上演。令他们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与欧洲戏剧节观众年龄偏大的现象相比,乌镇洋溢着年轻的气息。
直观来看,今年戏剧节期间人流密集,即便非周末也熙攘不绝,当一些古镇以传统业态吸引游客时,乌镇希望借文化内容留住人心。
当游客为“鸟人”而来,或为《人类之城》停留,在街头偶遇一场即兴演出,在戏剧集市与艺术家交流时,感受到的是一种“无处不戏剧”的生活方式。如今的乌镇并不单纯追求客流规模,更注重提升客单价与消费质量,进而实现整体经济效益的增长。潘杭认为,在新的旅游业态下,人们并非不愿消费,而是更愿意为真正美好、高品质的产品买单:“乌镇所坚持的,正是这样一条路。”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上海国际艺术节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拉动消费超44亿元
第二十四届艺术节主板演出票房达6593.76万元,吸引海内外观众14.09万人次走进剧场。

湘超永州夺冠,四线城市如何变“情绪红利”为“经济红利”|区域观察
这是永州面临的现实而紧迫的重要命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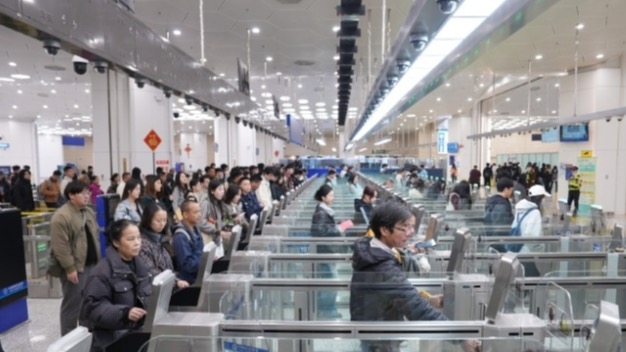
横琴口岸前11月入境外国人近40万人次,免签政策成引擎
今年前11个月,经横琴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达39.7万人次,同比增长82.6%。

东航“上海—奥克兰—布宜诺斯艾利斯”航线正式启航 “国博号”彩绘机执飞首航,开启跨洋文化之旅

文旅项目如何穿越周期,操盘手们带来一手经验
那些能够穿越周期、抵御内卷的项目,往往不是资本催熟的网红地标,而是从土地深处生长出来,与人的情感产生共鸣的美好生活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