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过什么样的生活,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选择、一种设计,也是一种对人生的投资。敢于冒险,还是安于稳定,既是一个人自身性格的因素,也受外部趋势的影响。
社会学家苏珊·克林专注于研究当代日本青年移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在新书《逃离都市的日本青年》中,这位北海道大学副教授采访了118名青年,探究2009~2017年间,这些年轻人为何离开大城市搬到乡村。在这些20~45岁的受访者中,有一些有海外旅居经验,有一些毕业于日本顶尖高校或曾在知名大型企业工作,也有一些人非常普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有个性化的生活设计。
在苏珊·克林眼里,“上东京”不再是日本当代年轻人唯一的追求,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迷恋在大都市进入职场,在终身雇佣制下追求职业理想,而是希望到乡村去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体验不一样的人生。这些受访者给苏珊·克林留下的最强烈印象,是大多数人不希望“被管”,厌倦“班味重”的职场,希望过上“真人感”强的生活,靠自己去创造一番事业。
中国当代青年中也有一些人在进行扎根乡村的探索,他们可以从日本稍早的实践中借鉴什么经验?苏珊·克林的观察和思考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参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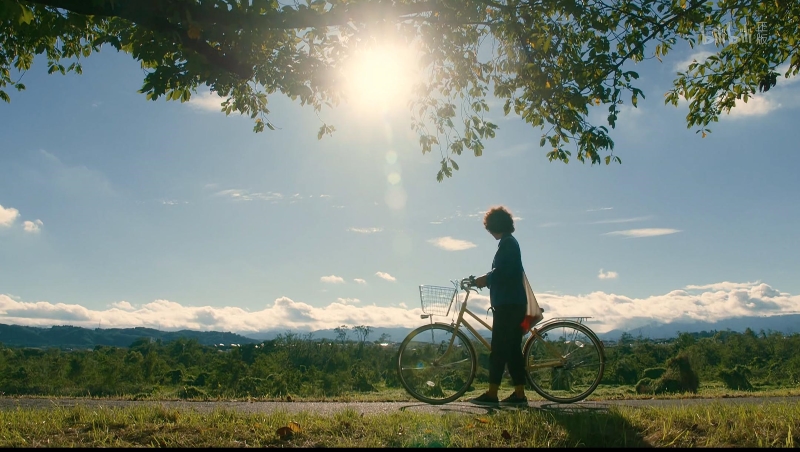
重新设计生活方式,既新奇也有风险
“可以马马虎虎过活,生活节奏很让人放松,这两种感觉交织在一起,就是我喜欢小村镇的原因。”在宫城县石卷市的一个灾后重建区,一位三十出头的移居青年告诉苏珊·克林,自己之前住在京都,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不久,他到石卷做救灾志愿者,此后一直没有离开。他开了一间小店,依托小店,他和当地人,以及很多来参与灾后重建事业、寻找新机会的外地人保持着联系。
在苏珊·克林看来,这位青年的心态有一种“边缘性”,他的态度决定了他不一定能在当地建立稳定的生活,但这种态度并非消极,而是蕴藏着巨大潜力,或许能为当地社群的中长期变化提供有建设性的新观念。她认为,当代日本青年对归属感和“家”的认识在变化,“你在的地方就是家,你在的时刻就有家”。
由于在乡村可以从事有益于自己和社会的工作,年轻人会有“心潮澎湃”的感觉,从而产生积极向上、灵感勃发和干劲十足的情绪。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从东京搬迁到一座偏远的小岛,她在2016年接待苏珊·克林时表示,在东京的时候,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购买衣服和各种商品,沉迷于花钱。“小岛很偏远,没法买到以前习惯吃的麦片,但可以用收获的或别人送的农产品,自己搭配早餐谷物。”
这位受访者说,在小岛上随时可以体验各种户外运动,这样的快乐是她在东京时从未体验过的。因为不再需要花很长时间通勤,在小岛上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大增,虽然岛上娱乐项目不多,却正好可以尽情享受自然。移居之初她有些不安,如今已经适应了新的日程时间安排。
书中写到的移居青年,有的开起了村里从未有过的新式餐馆,有的成为女性村民手工艺创业的领袖,有的改造空关的老房子并成功开了民宿,有的成了当地政府招揽渔业体验者的形象大使。
不过,苏珊·克林在访谈中也发现,一些青年在移居小地方时,原本梦想的是过“慢生活”,新工作干起来后,却比之前更忙,甚至工作量超过了自己在大城市的时候。这一方面是他们自我认同感提升的表现,是好事,另一方面,也有不少人在硬撑,坦陈没想到会这么累,以至有人很快就扛不住了。
还有的青年来到小地方本想做自由职业,却被困在了政府机关工作中,处处受限,离自己搬家前的预期越来越远。但在乡村或小镇,工作选择面不大,要么再次改变,要么忍耐。
真希在石卷市的一家纺织品设计店工作,这家店是一位来自东京的前救灾志愿者开的。真希的日常工作是按照店主的指示制作纺织品,并指导一名新员工动手制作。这份工作收入不高,为了维持生活,她得同时打三份工,每周有三个晚上要去一家餐厅工作,其他时间还要去一家酒吧打工。
三十多岁的真希是北海道人,她也是在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来到石卷的。到2017年,她在移居地的工作依然忙碌琐碎,几乎没休过假,也没有充足时间去社交和寻求职业发展。真希希望自己能维持好身体健康,等有时间了,想去接受厨师培训并考取职业证书。
想好自己要什么
日本第一批较大规模的“生活方式移民”,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不少年轻人移居冲绳,他们看中的是那里具有“异国风情”的自然景观,仿佛不用护照就能出国旅游。在苏珊·克林眼中,近十多年的青年移居者则是以新的方式在算一笔生活方式的账。农村生活成本低,空闲的房屋和有待激活的社会资本充裕,广阔天地大有可为。现在看的是谁更有创造力,能成功地展开创业项目或社会实验行动。
京都大学学者吉琛佳长期关注日本移居青年的发展问题。吉琛佳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到大都市发展的青年返乡、城市青年去地方或乡下发展的趋势,就已经开始出现。即便如此,现在“上东京”还是一种主流观念,而且由于交通更便捷了,过去可能会选择大阪、广岛、仙台等地的年轻人,会跳过这些区域中心城市直接上京。
据吉琛佳观察,地方移居趋势有一些新特点。比如,地方再生项目能得到地方自治体和财政拨款的支持,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参与,包括永续生态社会、技术赋权、互助社群、社会教育等议题,年轻人参与这些项目的未来发展预期,并不比到东京发展的人差。东京也在变得不那么“冷漠”,吉祥寺、高圆寺、下北泽、东横等一些区域,逐渐有“村化”的味道,出现联系紧密的熟人社会,成为闲散青年的聚居地。

在中国,相似的移居青年个案屡见不鲜。沈小姐5年前从上海移居云南大理,住在洱海边的一个村里。她告诉记者,自己从事的是生态科技与信息化工作,待在东部沿海大城市当然是好的,但云南的气候、环境、饮食吸引了她。大理的青年移居社群已经发展了三四十年,氛围不错,她已经交到不少朋友。她在江浙沪的业务比较多,但在云南的工作也在增长。秋冬季到春节前,她有时会去东部沿海城市做现场工作或参与活动。在江南比较难熬的盛夏,她主要待在云南。但沈小姐也感觉到,大理的社群能级有限,她关注的前沿科技议题能够对话的人不多。气候变化也给她带来了新烦恼,比如今夏云南降雨量大大增加,破坏了她院子里的植物园,需要花很多额外的精力去整修。
另一位李小姐,近年把一半的时间从常居地上海移出,放到了浙江沿海岛屿上的老家。她从事文化旅游相关工作,业务繁忙时可能每月有十多天需要住在岛上。她的一些项目包括将岛屿开发的潜力宣传到其他省市,并支持想到岛上做文旅或商业创业的外地青年和返乡青年。李小姐经历了重新适应家乡生活的过程,毕竟她已经在大城市的传媒行业工作多年,两地生活节奏和商业氛围差异很大。她告诉记者,长期观察来看,在岛屿上最容易创业的还是餐饮类项目。挑战比较大的则是需要外部公信力、强调知识产权的业态,比如设计,因为当地是小圈子的熟人社会,看重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对外部流行趋势不一定跟得很紧,有时会显得有些盲目和茫然。
城市研究者宋敖曾在过去两年中游历日本各都道府县,探访了数十个乡村和小镇,包括一些较为偏远的地方和灾后重建地域。在比较中日青年的移居乡村趋势时,他认为,日本的城乡差别相对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较均衡,比如村里也有酒店、便利店、商场等基本业态,只是服务的密度低于大都市。而在国内,离开大城市去乡村生活和工作,可能意味着很多基本物质条件需要自己想办法。
苏珊·克林在书中强调,日本社会对于农村地区发展前景、移居青年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农村变成了一种试验场,相应地,年轻人对生活方式也抱有试验心态,保持接受变化的积极心态可能是当下最大的特点。
吉琛佳也提到,在大城市和地方农村之间“多据点生活”的方式正在兴起,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远程工作普遍化,很多人开始在东京之外营造另一个生活据点,并来回移动,利用城乡各自的相对优势,展开一些创新的业务,相关情况值得长期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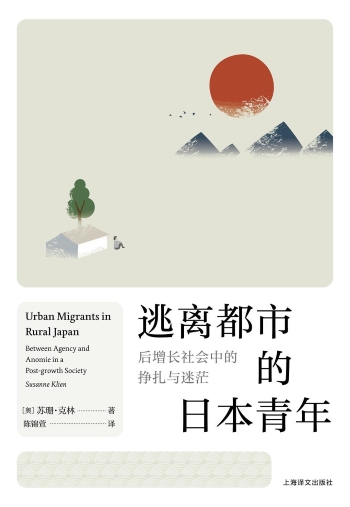
《逃离都市的日本青年》
[奥]苏珊·克林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如需获得授权请联系第一财经版权部:banquan@yicai.com
文章作者

武汉发布“江汉揽胜”主题游线
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

壹快评|“死了么”爆火背后,年轻人需要一个拥抱
“死了么”的爆火,提醒我们去关心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心世界。

投入9000万发消费券等,上海跨年迎新季全方位提振消费
本次跨年迎新季将从即日起持续至明年3月3日,横跨元旦、春节与元宵三大节点。

12省份旅游总收入破万亿,今年还有2省份在冲击
旅游产业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其在区域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也在快速提升。

53个国家级景区、年接游客近7000万,六安何以撬动千亿级文旅产业
“十五五”时期,六安将力争实现年接待人次10%以上、收入12%以上的增长;到2030年,全市年接待游客量达1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00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