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实|中国资本市场:龙马精神,未来可期|马年大咖谈
六大积极因素协同显现,共同构成中国资本市场中长期价值的坚实底座。

程实:美国经济的四重风险︱实话世经
制度性预期一旦发生扰动,不仅可能加剧货币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难度,还可能通过影响市场定价逻辑与风险偏好,放大宏观波动。

程实:全球生产网络与绕不开的中国︱实话世经
中国已经成为连接最密集的价值输出枢纽,并与美国共同构成驱动全球价值循环的双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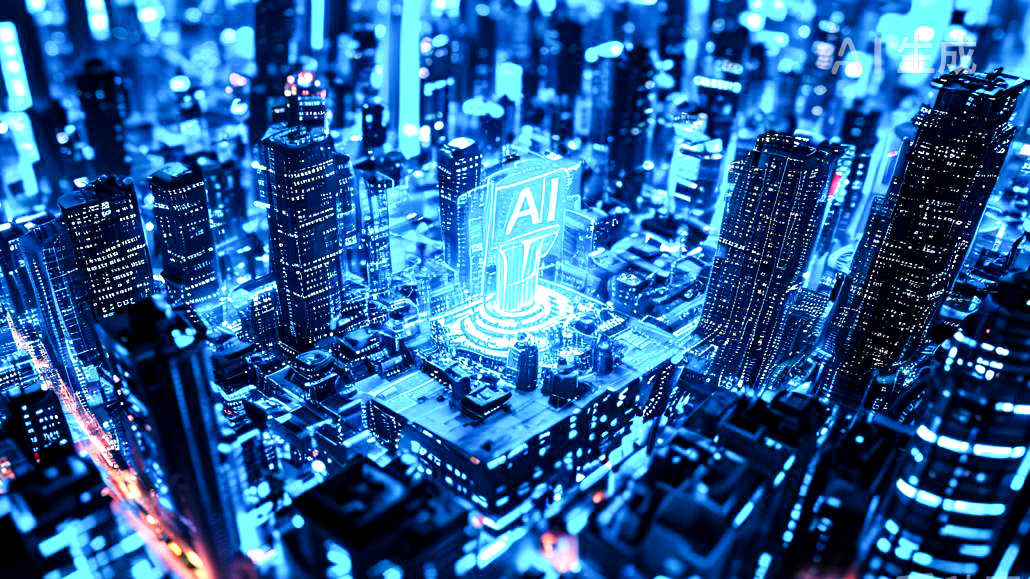
程实:AI让传统经济信号失灵,货币政策亟须前瞻布局
菲利普斯曲线斜率趋于平坦,贝弗里奇曲线整体外移,劳动力市场信号参考性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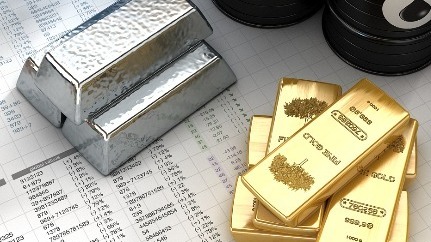
程实:银价震荡曲线揭示全球变局进行时
部分大宗商品在价格水平上出现阶段性突破,但趋势延续性并未随之增强。

程实:人工智能时代的中国比较优势︱实话世经
综合能源、人才和制度三条线索,中国均具备比较优势。

程实:中国如何走向中等发达国家丨实话世经
中国正在进入一个“底线稳固、上限打开”的新阶段。

程实: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Labubu︱实话世经
Labubu的走红并非偶然,而是代际审美、情绪符号与身份表达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增长进入人和物的乘法时代
从以扩大投资规模为导向的加法式增长,转向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相结合的乘法式发展。

程实︱2026年全球经济展望:在混沌中构建秩序
全球财政主导下,结构性改革、产业链重组与技术创新正在取代旧的全球化逻辑,重新锚定增长基础。

程实︱2026年香港经济展望:在交汇中重塑平衡
预计2026年香港经济将继续保持温和增长,GDP增速有望达到3.5%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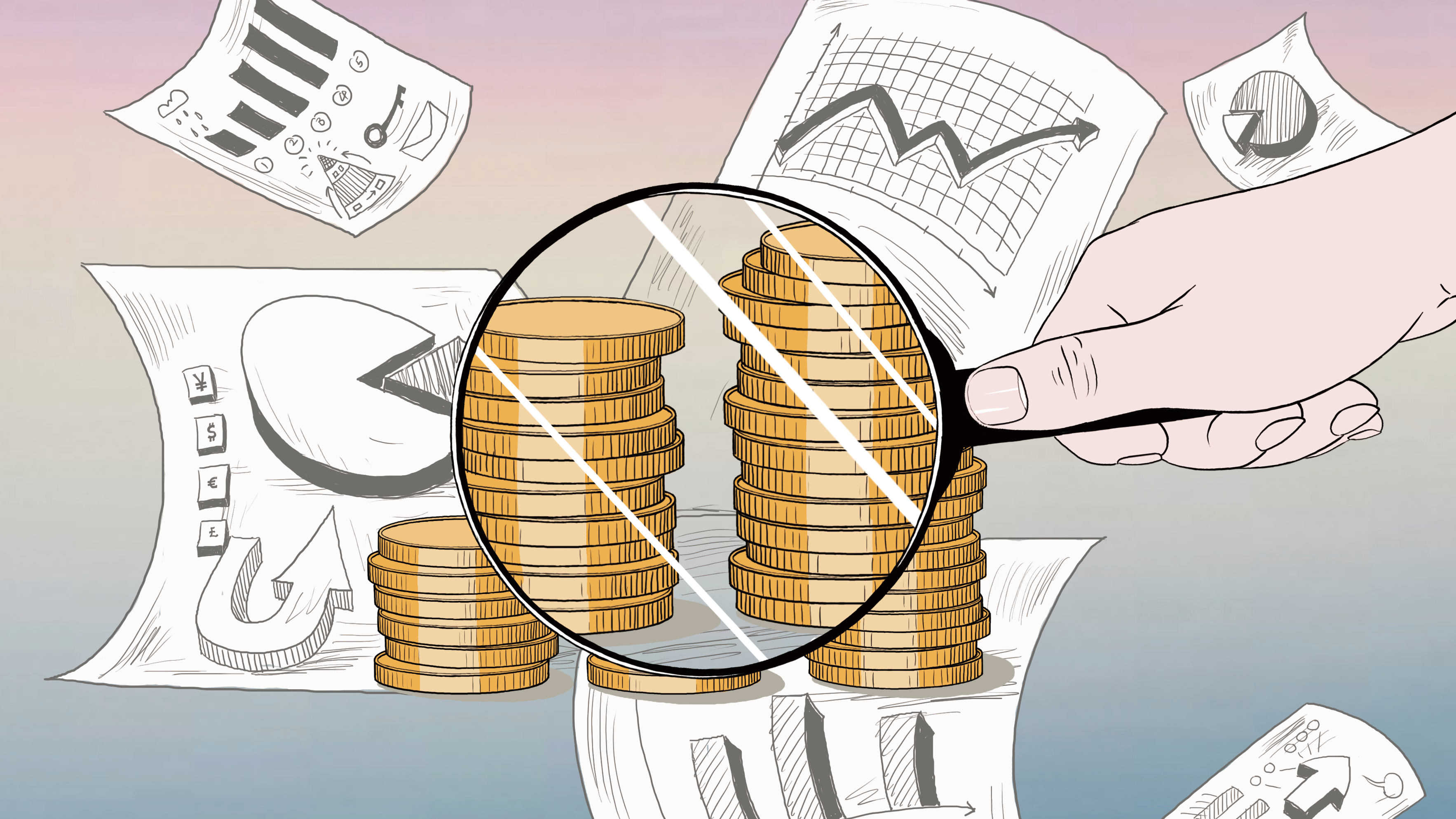
程实:货币政策跨境传导的美元渠道︱实话世经
央行不仅要权衡货币政策效果,还需兼顾美元汇率变动带来的外溢效应。

程实:在全球复苏反复中寻找中国式确定|国庆大咖谈
内生驱动,行稳致远。

程实:老龄化的债务幻觉丨实话世经
全球老龄化不仅推高了经济体的财政负担,也扩张了社会对债务资产的需求,并塑造了一种“高债务—低利率”的均衡。

程实:人民币未现系统性偏离,内核稳定支撑走势稳健丨实话世经
人民币当前运行状态与均衡水平未出现系统性偏离,反映出基本面与市场的良性互动。

程实:从经济学原理看“内卷”困境与“反内卷”路径
从表象上来看,“内卷”体现为企业间的“价格战”,而其深层本质在于价值创造模式的单一失衡。

程实:非农系统性下修再现,美联储降息预期飙升
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若出现连续下修,通常领先于实际经济增速放缓。

程实:地缘的围墙 创新的阶梯︱实话世经
在全球化放缓、区域化加深的背景下,创新与技术发展正成为全球经济体系在不确定性中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程实:美国联邦学生贷款偿付压力如何挤出消费︱实话世经
作为美国消费的中坚力量,他们如今将在偿还贷款与生活支出之间作出权衡,非必要消费被迫让位,或将对下半年美国消费表现形成明显抑制。

程实:协同三路径,五年可新增25万亿消费规模
中国消费增长的潜在方向不仅来自边际消费倾向的提升空间,也来自服务消费扩容与下沉市场的结构性机遇。

程实
研究部主管、经济学博士。现任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中国人民大学和安徽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