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到:
- 微信
- 微博


{{aisd}}
AI生成 免责声明
某个被偷走了赖以为生的锅而歇斯底里痛哭的女人,一夜之间突然消失的15万难民,被抛弃在街头等死的童军,火车飞驰而过的最后一秒抓起摊位上一切能抓住的东西拔腿就跑的人们……
在漫游、观察非洲30多年后,传奇记者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在《太阳的阴影》中记录的这些故事,是书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部分,却远远不是全部。他还写下了非洲那些不为外界所知的大屠杀、普遍的饥荒、儿童战争、不知何谓统治的统治者……他始终在尝试抵达、传达非洲的内核,那个口述历史、信奉祖先与神灵、拥有匀速旋转的永恒时间的世界。

“《太阳的阴影》呈现了历史与现实不断对话、神话与现实互相交织的鲜活世界。它带我们进入的这趟旅程并不轻松。”译者毛蕊说,正是那些残酷、直击历史、直击现实的甚至让人不寒而栗的片段,让她在刻板印象的裂缝中,触摸到了这片真实的大地,重新认识了非洲。
8月15日,第一财经年中人文书单在上海书展发布,《太阳的阴影》获评年中十佳好书。评委会认为:“只有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能写出这样一个裸露、汹涌、真实到残酷的非洲。”由波兰语直译的这部作品,将优美生动的描写与干净有力的新闻语言结合,译作精准传达了卡普希钦斯基的纪实风格与悲悯情怀。
毛蕊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波兰语专业负责人,也是国内仅有的六位波兰语博士之一。自2021年以来,毛蕊每年有译作问世,包括科幻作品《机器人大师》、自然文学作品《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传记《辛波斯卡:诗心独具的私密传记》、纪实作品《太阳的阴影》等。她形容翻译的过程就像在夜空中看到璀璨的流星,“但怎样把流星的美传递出去,让读者也有同样的感受?”经历这个艰难的过程,她找到了、传达了,内心会有持久的满足感,这正是学习语言、翻译带给她的美好。

第一财经:《太阳的阴影》是一本非常有力量的书,作为译者,你有什么阅读或者翻译的感受想传达给读者?
毛蕊:在我看过、翻译过这本书之后,觉得自己之前对非洲的认知是非常狭隘且浅薄的。除了热、沙漠、动物大迁徙等,就没什么印象了。所以看完这本书的最大感受就是,我对世界的认识太少了,而对自己的关注可能过度了。所以我真诚地向每一个关注这个世界、关注其他命运个体的人推荐这本书。
阅读之后,我知道了很多不仅新鲜,甚至很难理解的观念。比如说“时间”,卡普希钦斯基写道,非洲人对时间的观念和欧洲人不一样。在这点上,我们亚洲人和欧洲人是统一观念的,认为人受时间的制约,人与时间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这场冲突永远以人类的失败告终。但非洲人认为,人类在影响时间的形成。时间是由事件的发展呈现的,而事件是否出现,取决于人,时间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只有人参与了、事情发生了,时间才存在。
宗教和神灵的力量在他们的生活中大到难以想象。人类的活动要首先得到祖先和神明的允许;人死去后,会被埋在家里,通过这种方式继续和家人生活在一起。另一个让我觉得震撼、悲凉的事实是,非洲的死亡都是“复数”的,都是集体性的,都是大规模死亡的。
在书的结尾,卡普希钦斯基描述了一次与大象的眼神对视。他描写得太生动了,让我能感到大象的眼神是如此有神、有力量的一种目光,以至于我现在看到大象的图片会一种有不寒而栗的压迫感。之前我对大象的印象是温和的、笨重的,在动物园的围栏里慢慢地啃着干草。现在当我再说出“动物园里的大象”这句话,已经感觉到这是一种折磨了,而动物园里的大象永远也不会有卡普希钦斯基描写的这种眼神和精神。
第一财经:这样一个非洲,可能对大多数人是非常陌生、遥远的。
毛蕊:卡普希钦斯基描述的是四五十年前发生在非洲大陆的故事。虽然时空相隔遥远,我们对这片大陆也所知甚少,但我们读的时候并没有陌生感,也没有时代变迁带来的隔阂感。我们今天依然对所谓的“南方”关注非常少,但是卡普希钦斯基提醒我们,真正处于少数的其实是“北方世界”,生活在温暖气候中的人口才是世界的大多数。
书里讲到好几场战争、屠杀,而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包括现在,南苏丹依然饱受暴力冲突困扰,但几乎也没有人关注。大家都在关注“北方世界”,其实北方世界的中心就是白人中心。
书中记录了这样一个片段:有一天卡普希钦斯基听见一声绝望的哀嚎,一个女人的锅被偷了。她的财产只有一口锅,她早上去赊豆子,用锅煮赊来的豆子,所赚的钱让自己吃一口饭。锅被偷了,就等于她的人生被偷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被别人偷走一个东西,我们的人生就没了。如果这发生在任何一个北方国家,一定会引起非常大的关注。但它在那块土地上随时会发生,却从来没有人关注。
在塞内加尔,卡普希钦斯基遇到了一对来自苏格兰的年轻情侣,他们觉得和他们聊天的所有非洲人都在索要些什么,所以拒绝和任何人交流。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是这样产生的。但卡普希钦斯基知道,非洲人来问候你,提醒你注意安全,他认为自己已经是在关心你了,给了你珍贵的信息,应该获得回馈、交换。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通过写作,他在追求平等和尊重。《太阳的阴影》的波兰语书名叫Heban,Heban在波兰语中指非洲的一种木材——乌木。卡普希钦斯基在书中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描述,他在听脸上闪着乌木光泽的人讲述他们的历史,他们坚毅的脸上闪着光芒,“我不太能听懂他们说的话,但他们的声音是那么 的严肃认真。他们在说话的时候,认为自己是要对本民族的历史负责的。他们必须将历史完整保留并继续发展。……每一代人都是一边听着别人传授给他的版本,一边对这个版本进行修改,不断地改变、转变、修订和修饰它。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历史摆脱了档案的沉重,摆脱了数据和日期的严格要求,历史在这里呈现出最纯粹的、如水晶般晶莹剔透的形式——神话。”
第一财经:卡普希钦斯基这样一位传奇记者,他把自己的观察留在了书里。你认为他的文本有什么特点?
毛蕊:他的作品是纪实文学,但是很难当纪实文学去读,因为他的描写非常生动,引人入胜,让人身临其境,文学性很强。但你不会怀疑内容的真实性,因为他是一名记者,他没有夸大事实,而是用严谨又富有诗意的笔触真实地呈现非洲。
全书第一句话:到处都是光线。他的波兰语写作让你身临其境,他描述了从阴霾的伦敦飞到非洲大陆,之前还是雨丝打在玻璃上,突然你就被阳光包围了,那就是非洲该有的样子。
这本书从“光”开始,最后也以“光”结束:“此时仍是黑夜,但是非洲最闪耀的一刻也越来越近——黎明将至。”光对于非洲是决定性的,非洲文明的很多特点、人们的生活状态等,都和光有关。光也可能是理解这片大陆的重要钥匙。这种把纪实与文学融为一体的写法,是卡普希钦斯基独一无二的魅力所在。
第一财经:卡普希钦斯基的几本作品中,只有《太阳的阴影》是从波兰语直接翻译的,你觉得语言和一个民族的特点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毛蕊:有些作品因为出版和市场的考量,会选择从英语转译,确实在速度和传播上更快捷方便。但如果直接从波兰语译出,就能捕捉到一种独特而不可替代的气质,那就是我所理解的“波兰精神”。
所谓“波兰精神”,其实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波兰的历史跌宕起伏,民族经历过战争、分裂、压迫与抗争,这些痛苦和磨难塑造了他们独特的性格——独立、坚毅、勇敢,同时又带着深沉的感伤。正是这样的经历,使波兰文学常常带有一种既浪漫又理想主义的底色。语言不仅仅是交流的工具,它本身也承载了历史的记忆和民族的气质。波兰语的表达有时充满诗意,有时又凝重而坚硬,这种张力其实就是波兰民族精神的延续。卡普希钦斯基的文字中,那种对苦难的直面与对人性的深刻洞察,正是这种精神的写照。而作为译者,我希望中文读者也能通过这些文字,触摸到这种穿越历史与语言的力量。
第一财经:最近几年你的译作不断,能谈谈你翻译时的状态吗?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候?
毛蕊:我翻译一般在深夜,需要非常安静的环境,一个人整个沉浸在文字中。读懂的时候,就好像我一个人在享受漆黑夜空中璀璨的流星,而且它们滑动得非常缓慢,我有足够的时间去捕捉和体会它的光辉。但作为译者,我还要思考:如何把这份瞬间的美传递出去,让读者也能感受到?有时候我能看到那颗“流星”,却一时找不到恰当的中文去承载它,这就是翻译中最痛苦的时刻。但正是这种痛苦,往往也伴随着巨大的愉悦,回想起来总是幸福的。
《太阳的阴影》的翻译过程是比较顺畅愉悦的。而我在翻译第一部作品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机器人大师》的时候,常常觉得自己面临的是难以逾越的挑战。莱姆的作品中有许多他自造的词语,有人开玩笑说,可能波兰语对莱姆太简单了,所以他创造了很多有丰富内涵的词汇。波兰有一些学者是专门研究莱学的,所以在翻译的过程中遇到这种词汇我要去咨询专家,还用中文体现他想表达的意义,如果没有对应的,我就需要自己去造。
翻译莱姆作品的过程经常像荡情绪秋千,一开始不知道某个自造词的含义,要去咨询专家,冥思苦想之后终于获得其中奥秘,好像有一种力量把我推上了理解的高峰,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喜悦;但当秋千从至高点回到低处时,又会感到孤独——因为我还要思考怎样让读者也能体会到这种喜悦,而不必重复我的起伏。所以翻译对我而言,始终都是痛并快乐着。
我认为,翻译和教育、特别人文学科的教育是一样的,有某种“滞后性”:越是美好、越值得珍藏的东西,越是不会以直接、轻松的方式呈现。它需要经过努力、主动思索、不理解与理解,甚至受到一些挫折之后,心里才会沉淀出的一份持久的幸福感和满足感。就像我们看到美好的景色,会想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它其实悄悄印在我们心里,可能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几十年之后才会回应我们,让我们醍醐灌顶,照亮我们眼前的路。翻译也好,文学也好,书籍也好,都是这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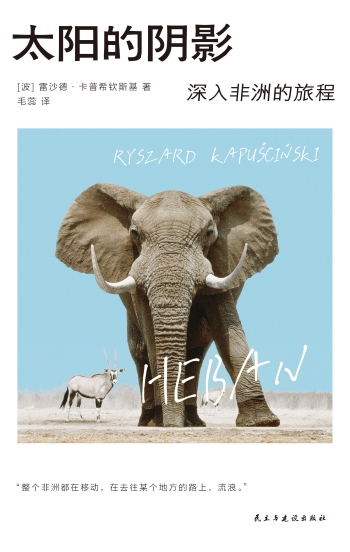
《太阳的阴影:深入非洲的旅程》
[波]雷沙德·卡普希钦斯基 著 毛蕊 译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理想国 2025年6月
文章作者

中国稻种在塞内加尔:巧织雀与睡莲共舞,还能守护“大米主权”
在塞内加尔实现粮食自给自足的道路上,来自中国的“绿色超级稻”正扮演着关键角色。

出海新变量|月均出口四万台设备,中国血糖仪企业叩开非洲市场
业务起步时充满挑战性。

非洲学者研究中国,除了基础设施还会关注哪些
赞比亚副总统纳卢曼戈邀请中国企业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框架,考虑赴非在医疗领域投资兴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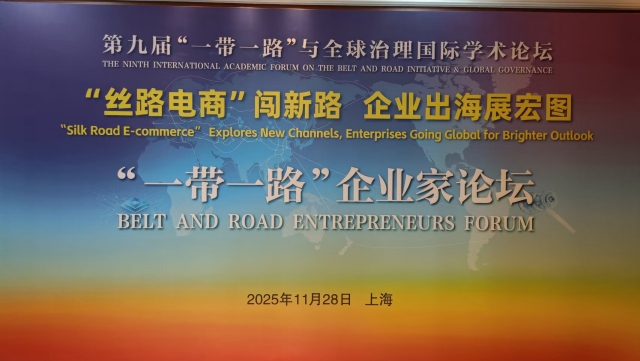
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升温,企业家与学者怎么看
今年前10个月,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34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3%。

从“年年买种”到“多赢未来”!中国“自留种”推动南南合作,孕育稻米新未来
中国如今已经是世界上农业科研最大的投入者。
